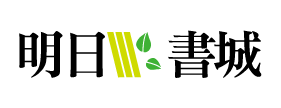會員登入
我要找書

-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推薦
- 目錄
- 內容試閱
特色
温世仁武俠小說首獎作家 黃健 深刻描寫當代中國人 虛擬之作
金蝶獎殊榮 小子 暴力設計
歷史不容猜想,那場浩劫、那個時代
並非真實史料,而是拼湊了破敗的深層靈魂
留給歷史的沉重包袱,心靈上的陰暗區域——
以及 這代人的意義
簡介
依當時的情況,人都已經拉到墓坑旁了,斷不會再活著放回來。
所有人都罩在裡面,人人逃不開……
他們是真實的法西斯主義再現——我終生也不會忘記他們看我們全家痛哭時的眼神,那不是人類的眼光,因為沒有同情,沒有打死人後的害怕和惶恐,甚至也沒有敵視和仇視,沒有任何不安,他們是一種在欣賞自己的傑作時的觀賞目光,非常冷酷和冷靜,他們是很清醒的殺人者。一邊殺人,一邊研究、觀賞自己如何殺人,這真是令人恐懼的一種事實。
今天社會的很多問題,都與我們這代人的靈魂失落不可分離。
因為我們沒法找時代討還公道,我們沒有可能懲罰一去不復返的時代。
我們懲罰的只有時代的後代,也是我們的後代。
黃健,祖籍湖北鐘祥,1966年生,現居湖北隨州。從事過很多職業,現是自由撰稿人。
生來喜愛好玩又有意義的事,有無限可能的事──武俠小說是,詩歌是,讀書也是。閱讀與寫作,正是我的兩條腿,它們不是讓我以達到某個彼岸為目的,而是讓我的整個行走過程,變得更有意義和無窮的樂趣。
生來喜愛好玩又有意義的事,有無限可能的事──武俠小說是,詩歌是,讀書也是。閱讀與寫作,正是我的兩條腿,它們不是讓我以達到某個彼岸為目的,而是讓我的整個行走過程,變得更有意義和無窮的樂趣。
土堆下的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附錄 黃健詩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附錄 黃健詩抄
作者自序
蒼涼
——《人證》代序
(一直想寫一本書,書名都擬定好了:《我與父親共用的辭典》,由幾十上百個名詞解釋組合而成。「蒼涼」是其中的一個詞條。)
我想以蒼涼為題,寫我的父親。不僅是我父親的個人命運,還有我與父親的關係。過了十八年,一個字也沒寫出來。紙上的空白,積雪一般,愈來愈厚,愈冰手。我小心翼翼,至於膽怯,不忍弄髒似的。
不著一字,是最佳文字——以蒼涼為題。
當然,這是機巧的說法。
我想我被外貌如雪的物質遮覆了。愈體會,愈無話可說——嘴巴硬如你空在那裡的床。這就是失語症吧。「在說與被說之間,對應了汙穢的冊封。」是我從前的一句詩。我看不單是汙穢,還有不能。我沒見過徹底的失語症患者,倒是經常處在不得不失語的狀態——我已經四十餘歲了,能說的事物如此之少。因為每個人都在拚命說出他們確信無疑的話:業內人的廢話,加注上笨伯(編按:對傻瓜的敬稱,一種調侃式的說法)解釋的信心。叫人厭倦得不行。
活著就不可避免是無須解釋。「不知生,焉知死?」其實不如說 :「不知死,焉知生?」因為解釋權永遠擱在亡者的布兜裡,被奔走的死神帶在身上。如果我的父親還活著,快九十歲了。可惜啊,我們之間就阻隔了那一個:蒼涼。
我不認同漢語辭典對蒼涼的定義:淒涼。不是那樣的。淒涼是做不到;蒼涼是能做而不做,也是明知不可做而去做。蒼涼入世,淒涼出世——哦呀,看來我也是笨伯中的一員。因為當我試圖解說,蒼涼已蒼涼地改變了。我感受它的變異,但我說不出過程。能夠言說的蒼涼,還是蒼涼嗎?能夠言說的世界,還是那個世界嗎?所以蒼涼不是淒涼,也不是那一個的蒼涼。大概蒼涼也不是阻隔在我與父親之間的那一個吧。
然而它不是蒼涼又是什麼呢?
在我父親去世後,我也不是什麼都沒寫過。我寫悼詞,字斟句酌,在父親的追悼會上,一盞熾亮的大燈下,我大聲唸,黑暗的後面,有幾百個人,包括躺著不動的父親,靜聲聆聽。親友席間偶爾有一兩聲抽泣,我不知是誰。後來有人說:「你說的真好黃健!」然而我知道並不好——我沒有足夠的坦誠與勇氣選擇。譬如:我其實什麼也不用說。然而我還是得說,並且說了,那就是蒼涼。我說不清它。
我也寫過一封信,偏執、刻薄。寄給外地的大姐。她讀了。我知道她讀了,但她不回信,見了面也不談它,而是談起了隨信寄去的一張照片:你那時還不到二十歲吧?等等諸如此類,如同在談當日的天氣。再後來,我父親去世八九年之後,我寫了一組詩。有一首叫〈但是,這很虛假〉:
逃避白晝的脅迫,
我試著向夜空說話。
我試著在夜空
在我的話下面,
像星光:荒涼屹立著燃燒。
我試著撕裂那空明的皮,
只到看見盛人的床鋪
密匝排列如戰利品。
在夜空下
你的透明有了背景。
像在燈光昏暗的候車室外
等候那漆黑的鐵軌線,
放下一個旅客。
幽會握住
月台的冰涼小手。
眼睛的光焰
輕輕閃爍。
那穿破夜空帶著夜空
進入我耳朵的我的話,
像飛逝的夜行列車。
窗內林立
瞠視的星辰。
我燒紙——
火帶走火也交回。
但是,這很虛假。
再沒人敢在世上像你那樣揍我。
惡恨恨,往死裡打。
不,這也是一句虛假。
你至多預支了沉默。
夜空那樣不回答。
八年了
我一次不夢見你。
十三年了
我未和你說過話。
我消除星空
試著在體內說話。
如果我聽到你也應聽到。
為何諒解和寬容
總在諒解和寬容沒用之後?
為何沉默
總在沉默失效之前?
但是,父親啊
這很虛假。
似乎比寫給大姐的那封信要寬厚一些了。因為漸漸地,蒼涼已經進入我的內心。我感到世事內部的虛假。不過如果將虛假置換上蒼涼,這詩就寫不出來了。
有那麼一天,夜裡停了電,窗外月光如水。不停電的話,這如水的月光就該被我慣常忽略了。說月光如水,並不確切。其實是我站在陽台上,看月亮與它的輝光,身體如水一樣沁涼。夜幕在月光的背面,確實像蒙了一層皮。我想看清它。
自然,我看不清。
那裡大約是父親居住的地方吧。我當時這樣想過。同時知道我的想法很虛假、很不科學,像孱弱的自我安慰。
然而單是科學,並不足以叫我安寧。童年之後,唯一能使人安寧的,我以為莫過於蒼涼。童貞與蒼涼,除去它們,人生的本真狀態是不存在的。
我的父親不在世了,我們的父子關係不會結束。它還在持續發生:那就是愈來愈深長的蒼涼。
(《人證》與我父親的淵源極深極其隱密,但它是小說;亦不是我的家族自傳體小說。我姐姐曾撫摸手稿說:你塑造了一個理想中的父親是吧?
我不吭聲。對這種說法,我也有些厭倦。
我再次感到蒼涼——世上沒人看出我父親在《人證》中的深藏不露的存在。然而這就是事實。〈蒼涼〉是我寫給父親的詩篇,《人證》是我寫給中華民族的詩篇。有時我就是覺得,它們是同一首詩。)
精采試閱
土堆下的序
從春天到秋天,土城牆上樹草森森,斑鳩、烏鴉、野鴿和大群麻雀活躍著呢——有一年我開始寫詩,突然寫出得意的句子:「一棵樹上鳥堆如雲,牠們總是嘰嘰喳喳,牠們總是搶著與我攀談,牠們總是嚷:『他在這裡嘿!』弄得我發一陣子窘。」後來想想,那是什麼鳥?麻雀吧,似乎也只有麻雀才這般熱情和多嘴——小鳥們在樹梢穿梭飛躍,蒼鷲翱翔在雲端,草叢裡有野兔、蛇和蟾蜍;斜緩的小路拴上山羊,黑的、白的,瘦瘦的,就是不拴放羊人。太陽東升與太陽西落,城牆上的樹林為半個小城抹上樹蔭。一九八一年,這條蔥綠的碎花帶子消失,拆除了。那一屆政府,真沒說的——他們由寫拆城報告和核准報告的人組成。我父親算其中一員。他們那代人,真實得很,大公無私,腳踏實地。這個,真沒說的。
後來,不出十年,到下輪政府,就後悔。那時我們小城拆縣改市了,其實底子還是本省最大的縣,地盤大,農業人口多,農副產品依然是地方經濟的大頭。建市,只能說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對工業化進程的渴望甚是強烈。他們未必就懂,也不一定非要懂,建設也是破壞的辯證道理。那一年,本市申報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來了幾批考核專家,專家們說:「土城若在,你們不申報我們也會給你們歷史文化名城稱號。」——這麼完整的土城在全國、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何況此城在《左傳》裡是有明確記載的。我父親這時離休了,他說:「這話兒怎麼說的!老子不愛聽。」——難道幾十年的工作都瞎搞了?!
我無話可說——您愛聽又怎樣呢?一圈土城和它的護城河只剩下我家後面的一截還在。一個突兀的大土堆沒毀,過去和現在它都叫「飛來土」,我家就屬飛來土居委會或飛來土社區管轄。飛來土是有民間傳說的,流傳了幾百上千年,故事說它一夜間橫空飛來,落在城西河邊,幫助大禹鎮水。這個當然啦,神話唄。可是,它並非因神話才未拆——它碰巧是國家測繪局設立的地球地理標誌之一,這下地方政府可管不了它啦。我從家中四樓的窗戶望出去,已不是我兒時的土城牆了,大樹傾倒伐光,荒草萋萋,像一座盜掘過的大墳塚。
土城上那麼多的野菜野草:將軍草、包袱花、甜地丁、艾蒿——我奶奶和我,她有雙小腳,拎著篾簍走在前面,我敲打一把小鐵鏟跟在她身後,我們低頭挑摘地菜。我們本地人稱為地菜的,學名叫什麼?我至今仍不曉得。地菜包餃子和豆皮春捲,鮮味殊為特別。我奶奶這人,有時突然想起她做的某事和說的某話,那感覺真叫聰明。她沒上過一天學,貧苦山區人家的女兒,讀不起書,可是臨去世前十年,近八十歲的人,居然還翻閱我父親帶回家的紅頭文件和一字一句讀我姐姐從大學寫回來的家信。信讀得結結巴巴,有時候還斷錯句,讓我們和她自己噗哧發笑。她耳聰目明,不戴眼鏡,那種老花鏡她可用不著。遇上不認識的字她就問我(從未見她問我父親或哥哥姐姐,等也要等到我回家才問,奇了怪,就是認准了我這個小老師),碰上我也拿不准的字,馬上查辭典。她總學不會查辭典——她笑:「你奶奶蠢得出奇哩。」我從不那樣想,我還沒那麼傻嘛!我父親的某些文件是有保密級別的,他說:「媽,那些妳不能看!」我奶奶瞅著她兒子說:「連你老娘都瞞的事,能有什麼好事?」一條多麼樸素的真理!我父親當即啞口無言,陷入他自己特有的莊嚴沉思——他又借此想得很深很遠。不過要我說,也想得太晚了點。我真喜歡那種狀態的奶奶,別看我父親威風八面,可在我奶奶跟前,常常傻眼。我奶奶教我識認很多野花野菜,其中大多數都摘回家品食過了——抄過沸水,涼拌上麻油、鹽,灑上少許辣椒粉,基本上就吃野菜本味,非常不錯,我一家都愛吃。
在城牆頂部的林間,太陽照著我們祖孫倆兒,我們走很遠、很遠,有時是走整個一下午。那年頭兒風的味道極其清淨,天特別藍,天空就像草原的天空,藍天白雲,很近,觸手可及。如今奶奶不在了,土城牆也不在了。那些菖蒲、蒲公英、川草花、石竹子、馬蘭花……也不在了——我從未產生那種慾望:縱身跑上飛來土,從雜草中再次找尋它們。那些我在野草野花叢中見過的灰免、蛇和山羊也不在了。自然,再也沒有了如雲的鳥堆。
再過幾年,也許根本用不了幾年,現在就那麼多人天天看見飛來土而不知其來歷——它可是從春秋時代就堆立在那兒的古城牆。那些或赭黑或灰黃色的土坷垃就是兩千多年前的文物。可是,說這個有什麼用呢?沒用。沒用就別說了。它的完整好像只存在於我的記憶裡,裹挾上許多、許多無以辨析的雜質。
第一章
衛生大掃除
我開始記事時,土城內的每戶人家週末都參加義務勞動:一家至少出一個人,大夥兒帶著臉盆、鐵桶、抹布、笤帚、鐵鍬和板車,午飯一過就集中到巷子口。男女老少,說說笑笑,齊心合力,灑水、掃地、撮垃圾、擦洗臨街面的玻璃。晚飯前戴「縣愛衛會」紅袖章的人會逐條街道仔細檢查,現場評出衛生等級。我家所在的胡同連續十幾週得到「特別衛生」的流動小紅旗,算最高榮譽了——特別衛生以下,是比較衛生、一般衛生、不衛生和衛生最差。比較衛生是紅紙黑字,一般衛生是黃紙黑字,不衛生和衛生最差是白紙黑字。沒人喜歡白紙小條貼在自家的巷口——彷彿那是流配犯臉上恥辱的刺字。那時人們的集體榮譽感非常強,儘管是很鬆散的一種集體——鄰里們。
街巷、屋簷、街門口、庭院、公共廁所和小合作商店都打掃得一乾二淨——鋪街的青磚和鵝卵石地面異常潔淨,一個泥鞋印也不會有;那些未鋪磚石的裸地坪掃刮得連一粒砂子都得勾腰才看得清;而且那些砂子你掂捏了看,也非常潔淨,就像是從河底撈上來的。這時距那一夥人人手裡拿著筆記本和圓珠筆、邊看邊記,彷彿記者、彷彿幹部觀摩團的愛衛會工作人員到來,還有一段忽長忽短的時間,這時候最怕誰家突然新生了垃圾,遺落到街上,哪怕幾片菜葉或一小撮撕碎的廢紙片,那就毀了——街道上的居民人人臉皮變色:愛衛會的人眼睛毒得很——我們前功盡棄了唄。所以義務勞動後,街道就派人看守,像守護晒穀場上的糧草。孩子們特別喜歡幹這事,因為臂膀上也箍戴一個紅袖章,袖章上有街道縫紉社刺繡的七個漂亮金字:「飛來土衛生監督」——這七字居然同紅衛兵三字一樣,不知縫紉社的哪個繡花能手靈機一動,選擇了毛體書法,好像遠在北京的毛主席親筆為我們這個小胡同的衛生工作題了字。這個繡章就不簡單了,它戴出來不久,便被愛衛會的工作人員看見了。應該說他們、其實包括那時的所有人,政治敏感和嗅覺,異常尖銳。他們立即彙報到縣革委會,縣革委會頭頭章節烈親自抓了典型,飛來土的紅袖章就在全縣,名噪一時。
我們家的老朋友章節烈
章節烈與我們一家十分熟稔。他比我父親小幾歲,照我父親的說法,他應該是舊戲裡的才子型人物,一個白臉書生。(這種說法其實有些武斷,我們以後會發覺並且疑惑:並非完全如此吧?)不過我們都承認,他若做中文系教授,一定勝任。《楚辭》和漢魏六朝古詩,他倒背如流,唐詩宋詞更別提了,《唐詩三百首》和《婉約詞集》,翻哪頁他背哪頁,連注釋都不放過;我親耳聆聽過,他有這本事——小錢鐘書似的——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行政口,那就是大才子了。而且對詩的內容,他有自己獨到的看法。譬如《詩經》〈螽斯〉,他從詩句的節奏入手,以為此詩是當時的說唱詞。他長篇大論,滔滔不絕,他的話倘若記下來,就是篇關於〈螽斯〉的小論文。他連背誦帶表演,比較有說服力地說明它是遠古先民們的三句半——「作者巧妙地處理了諷刺與調侃的分寸,所以它既譏嘲了聽眾,也娛樂了聽眾。那些聽眾可都是當時的統治階級奴隸主哩。」他說。
三句半是什麼呢?它是改革開放前社會上流行的、今天已稀罕絕跡的、沾染了調侃戲說味道的文娛表演形式。伴以咚咚咚鏘的鼓鑼聲,四人台上說唱,前三人正經說事,末尾一人歪批半句,精華盡在這半句,極顯機智幽默滑稽風趣,所以每每逗人譁笑。我還記得「四人幫」倒台後,我親身參與的一次三句半表演。我那時讀小學五年級,打得一手好鼓——傳統鼓點,咚咚鏘之類的。我和班上的另外三個男同學邊敲鑼打鼓邊穿插走台,每人一句台詞:
第一句:四個小人一個幫;第二句:姓王姓江和姓張;第三句:還有一個姚豬頭;咚咚鏘,咚咚咚咚咚咚鏘……我們得等一等,因為台下的觀眾很明顯,早就在期待那總是出人意料的後半句。所以押尾的後半句有時要搶著說,有時卻要吊一吊觀眾的胃口。我們咚咚鏘采重響一圈,再說唱一遍,好像說後半句的那人忘記了台詞,這時終於記起來:
四個小人一個幫;
姓王姓江和姓張;
還有一個姚豬頭;
滷肉。
滷肉的說法顯然有失雅訓,但小學生水準嘛,又在那個年代,還是很有效果。台下立即哄堂大笑,連坐在前台觀看演出的文教局領導也絕想不到我們這樣比喻,咧嘴大笑。
多年後我聽著老年的章節烈(那時他是市委黨校退休的一名普通教員)嘴裡發出咚咚切、咚咚切、咚咚咚采切、咚咚切……那些節奏,聽到他唸出的詩行: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我有些認可他的見解——我確實不能說它與三句半沒有明顯的相同之處。讀〈螽斯〉,它至少也是種視角吧。
可是,在多年以前,在章節烈遇上我父親這個伯樂之前,並不走運,他被埋沒在一個偏僻的小鎮,連轉為正式幹部的希望都沒有。他那時叫章吉利,在一座鄉村小學做民辦教師,臨時被借調到鎮黨委做文書。黨委文書居然是非黨員,有些怪,說明小鎮裡確實沒有人才。我父親去他們鎮聽鎮領導彙報工作,發現了他,對他操筆的彙報材料十分賞識,抖動材料對鎮黨委書記說:
「這筆字可不得了,不見得比郭老差哩,我看是飽讀詩書的。什麼成分?」
那時的鎮委書記嘛,多數同我父親類似,是以大老粗自居的工農幹部。他說這個章吉利可有些讓我們犯難哩,貧農是貧農,還是窮到根的人,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父母雙亡,孤兒零丁苦命一個,可在他居然是在大地主家裡讀書長大的——他姐姐給當地一個大地主做小老婆,把流離失所的弟弟領回家撫養了幾年。
「同地主的兒子一道,」鎮黨委書記說,「章吉利也被人喊過少爺哩。」
我父親說:「根子還是窮根嘛。人啥樣?」
鎮委書記說他人還不錯。既不窮酸,也不驕傲,階級立場是端正的——與地主一家斷絕一切關係;是個追求進步的青年。
我父親那時按實際年齡也算青年,可是他十二三歲參加革命,在新四軍第五師師部當通訊兵,與很多大首長朝夕相處,與他們「一個鍋裡搶過鍋鏟」(一句世俗老話,表明彼此淵源很深。我父親也確實這樣說過:「某某某同志,我們還相互搶奪鍋鏟的呐。」那個某某某同志當然是聞名全國的大人物。)十幾年後他當了縣級領導,就有點老革命的派頭了。他說:
「這人我看可以培養。他父母死於貧困,他不會不仇恨舊社會。雖說過了幾年地主生活,也是寄人籬下——這可不同於地主崽子。在地主家他姐和他,都沒地位,也是被壓迫階級嘛。再說了,我們共產黨人要改造全世界、全人類,胸襟比海都大,哪還容不下歷史上有點小問題的人——你們要考驗他,爭取培養他入黨。他有才啊夥計。人才難得啊夥計。」
我父親還說:「他名字得改一改,什麼吉利不吉利,封建主義。我看叫節烈吧,就是要有共產主義節操,就是要向革命先烈們學習。章節烈,很好嘛。就這樣吧。」
章吉利——以後叫章節烈,他的命運就此發生了改變,不僅入黨、提幹,沒過兩年,就被我父親點名調到身邊做祕書。章節烈那時經常出入飛來土胡同,全胡同的人都認熟了這個疾步如飛、笑咪咪的縣委章祕書。他後來成為權威顯赫的縣革委會一把手,變成已下台的我父親的領導兼保護人,完全靠他自己的機緣和運氣——他乘上了時代的浪潮,可是世上沒人會永遠坐在那些變幻不定的浪潮上。
章節烈接到縣愛衛會報告,輕車簡從,微服私訪。他週末獨自騎了一輛破自行車,匡匡鐺鐺來到飛來土,支起車,扯起衛生監督的胳膊仔細看那個紅袖章——他不動聲色,面無表情,一聲不吭,翹腿上車,匡鐺來又匡鐺鐺去,神威莫測。他當然被戴紅袖章的人認出來,那人發起了呆,然後他突然嚇得夠嗆,虛汗滿面,渾身發顫。他取下袖章,不敢揉成一團,雙手捧起如捧自己攤薄的、破上一個大洞的命運,狂奔進居民小組長衛紅旌家裡:
「闖禍、闖大禍了!」他說,「縣革委會章主任來了!」
衛紅旌三十歲左右,是個精明能幹的街道女幹部,她說:
「章節烈?我沒接到通知呀。他來幹嘛?」
那人說:「看了袖章扭頭就走,臉陰得很!」
衛紅旌嚇了一跳:
「袖章?袖章怎麼了?你戴反了?」
「不是呀!」那人說,然後放低聲音,「我們會不會在偽造毛主席題字?」
衛紅旌的反應快得很,著實嚇了那人一大跳,她的兩腿突然癱軟下去,一屁股滑溜到地上後,兩腿就僵硬發直不能動了,她兩眼也僵直,眼淚鼓湧而出。她虛弱地、生命衰竭地、瀕死一般地說:
「偽造主席題字?我們怎麼會!我們怎麼敢!我們不要狗命了嗎?」
那人把袖章恭恭敬敬地攤放在衛紅旌的書桌上,小心翼翼地拿一本《毛澤東選集》壓住,不敢看她。他蒼白著蒼茫一片的臉,盜賊似地側身溜出她的家門,跑過胡同,鑽回家,消失了,他躲開了,十天半個月內不露面了。於是這個消息很快就瀰漫了整個胡同,人人都有大禍臨頭的恐懼,大家天一黑就關門閉窗,連電力不足的湯黃燈光都不對外敞開了。
這樣等了十天,半個月,度日如年。衛紅旌整日虛白臉,蓬頭垢面,對著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喃喃自語,默默流淚;如果再多半個月,她可能就真瘋了。可是正好半個月,在章節烈私訪飛來土的第十六天,城關鎮革委會的頭頭腦腦一大堆,敲鑼打鼓,燃放鞭炮,領著下屬其他單位的幹部群眾、裹雜著看熱鬧的路人和放學的中小學生是另一大堆,他們給飛來土送錦旗來了——錦旗上也鏽有七個金光大字:「毛主席的好戰士」,旁邊是一行小黑字:「頒給縣城關鎮一街飛來土居民小組」。這事立即變成一大喜訊,像攜帶了花籽的春風,刮進飛來土所有人的家裡、心裡了。
原來章節烈主任剛在全縣三級幹部大會上大力表揚飛來土居民小組的紅袖章——那是一種革命意願的表達,那是對毛主席的無限敬仰。
他說:「他們連打掃衛生都不忘與捍衛毛主席、捍衛黨中央的革命思想相結合,我說他們就是毛主席的好戰士!」
實事求是地說,章節烈把這事上綱上線,拔得太高了。衛紅旌披頭散髮,淚如雨下,大喜狂笑——她在毛主席像前的祈禱應驗了——她覺得她的那些低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聽見了。她舉臂高呼:
「毛主席萬歲!偉大正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飛來土的居民們也山呼海嘯。
這個紅袖章,這個在衛紅旌的夢中曾經變得像一張神話傳說中的紅飛毯,金光閃耀地托起她飛往北京的紅袖章,立即被送往全縣三級幹部大會現場——它被陳列進一個玻璃櫃子,與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一起,供幹部們參觀、學習。飛來土縫紉社不得不加班加點連夜刺鏽了一個同樣的新袖章——接著,就不止一個,而是幾十、幾百個了,後來差不多縣裡的每個最基本的組織單位,一個生產小隊、一個車間、一個班級,都來飛來土縫紉社訂購毛體字的衛生監督袖章。縫紉社的工人們用一個多月的時間賺夠了差不多一年的工資,她們忙壞了,縫紉機在她們飛奔的腳步之下噠噠噠通宵響個不停,就像是一個人日夜不停的鏗鏘笑聲,她們喜壞了。
衛紅旌立即被提拔為城關鎮一街革委會主任,得以參加這次三級幹部會。我父親也是這次三級幹部會的受益者,他從靠邊站被結合進縣革委會,擔任主管全縣生產的副主任——我父親此後半生再也沒擔任過正職,這讓他有時想一想也不免鬱悶。
「沒有文化大革命就好了,我早就升到副省(部)級了。」他說。
我父親不是一個自吹自擂的人。可是我確實親耳聽他說過這句沒勁的話——近乎哀悼、賭氣、自暴自棄的話。
其實衛紅旌不是別人,她是我的小姨,我母親最小的妹妹。章節烈當我父親祕書時,她還非常年輕,驕傲得很,是位頭頂紅星、身披紅旗的公主。章節烈曾經徒勞無益地追求過她幾年。我不知當她面對毛主席畫像祈禱時,惶恐的她是否做好了承接章節烈公報私仇、打擊報復她的準備,那裡是有命運的最壞結果的。所以她後來對章節烈的感激和尊敬,恢復了一個女性的柔情,不是時間能輕易改變的。
章節烈力保我父親,在老一代領導幹部群裡為他自己掙了不少上佳印象分。就連當時省裡幾位結合進省革委會的老領導也因此對他刮目相看,覺得他不是一般的、那種一無是處、忘恩負義、純粹的造反派。不過我父親好像並不很承他的情。他此時對衛紅旌當年拒絕章節烈一事表態說:
「那時我內心是同意你們結合的,妳不幹,這事未必是壞事!」
衛紅旌一臉茫然,聽不大懂的樣子。要再過上許多年,我們才會發現,我父親眼光深邃犀利,是能穿透時間和世事人心的繁花屏障的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