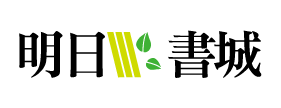-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推薦
- 目錄
- 內容試閱
特色
施達樂最台、最現代的新武俠小說,卻帶引我們回到那江湖誕生之初,武俠萌生的源頭,讓我們重新思索武俠的本質、江湖為什麼存在……
──知名作家 宇文正
俠氣鋒銳似劍,卻又兼寫草莽英豪之可親,施達樂的作品傳承了通俗傳奇文學的精髓,是今日武俠小說界的寶物!
──知名小說家 喬靖夫
台灣英雄俠客何其有幸能獲小說家的生花妙筆而活靈活現。在歷史容易被遺忘或扭曲的時代,此乃台灣英雄之褔,也是台灣之福。
──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 譚劍
簡介
隱身市井 絕技祕藏
乃賴、冬陽、宇文正、喬靖夫、陳浩基、譚劍、譚光磊 一致推薦
得獎無數、台客武俠創始人施達樂,首本短篇集作:取自《時代周刊》人物陳樹菊、跆拳教練鄭大為、台灣之星徐若瑄淚灑東京影展等八則勇氣故事。那樣的時代,暴力與不義,俠心一起,力抗命運。
劍沒有強弱,用劍的人才有強弱;
劍不在長短,志氣才有長短。
台灣人是世界級的人物,哪一國都一樣。
──台客武俠創始人 施達
不屈劍刺竹
取材自台灣跆拳教練鄭大為犧牲了國際裁判資格,只為正確的判決與運動專業而戰。第六屆温世仁武俠小說大獎短篇佳作。
祕劍阿菊
取自《時代周刊》世界百大影響人物──陳樹菊。地方豪強想要徵收阿菊以畢生積蓄所奉獻建成的兒童教養院,從牢中放出了少林鐵頭功惡徒………
清風搏浪
劍道師父余清風與日本軍人池波之女阿雪隔屋扶持,相依為命;兩人陷入了身分與國族認同的危機。
忍劍旯犽
取材自法官輕縱侵害女童嫌犯一案。純樸的鄉民手持白玫瑰在法院門口抗議,就連荖濃溪水彷彿也在不平地怒吼著!
姬劍若喧
改編徐若瑄東京影展淚灑事件。總督府為了宣傳治績,拍攝撫番影片「真正的人」,女神般的阿德麗自暗夜燈火下降臨,唱起了排灣族的戰歌。
祕劍鶺鴒
飛鳥流高手郭吉罹患惡疾引退,擔任雜役維生,某宴巧遇多年前仳離的妻子,因搞砸了婚禮而遭陳欽打傷………
浪速浪槓
改編自撞球王子吳珈慶變更國籍案。日本海軍浪速艦在雞籠發掘了撞球天才少年阿慶,欲強行徵召他入伍………
老劍蠹龜
取材自著名社會事件「陸正案」。老人習劍十年難有突破,當他得了祕劍,向著桐花如雪飄落的客庄而去,用老邁的雙手,求取最終的正義!
台灣阿猴人。台大商學博士、康乃爾電機碩士、台大電機畢。專長科技管理、多媒體系統等,學術著作23篇(含SSCI)。創辦科技事業數家,數年前悟「謬作京華名利客」,封劍歸隱,返鄉教書至今。好打電動、妄議嘲世。以司馬遼太郎為師,寫俠寫志,樂此不疲。
推薦序 ◎ 乃賴
自序:說故事的人
不屈劍刺竹
祕劍阿菊
清風搏浪
忍劍旯犽
姬劍若喧
祕劍鶺鴒
浪速浪槓
老劍蠹龜
不屈劍刺竹
祕劍阿菊
清風搏浪
忍劍旯犽
姬劍若喧
祕劍鶺鴒
浪速浪槓
老劍蠹龜
後記
附錄俠客QA ◎ 施達樂vs.譚劍
作者自序
自序:說故事的人
「自由」與「命運」是一組看似相反的概念。身而為人,我們怎可能又自由又被命運拘束?又怎可能在命運(神?某種更高的意志?)如傀儡般操弄下,成為擁有獨立自由意志的人?
諸君可以想想你還是個窮學生、或失業、流浪的時候;往往就是你一生最富有創造力、充滿了夢想與希望的時候。又窮又瞎又聾、一無所有、被囚禁、被威嚇、被折磨……時,最能感到宿命的悲哀、命運的作弄。
反過來說,最隨心所欲、最自由的時候,往往也就最常被命運作弄:終於得到最愛的女孩,就等著被她使喚折磨;終於找到理想的工作,就等著被上司耍弄;終於可以上街丟石頭,就等著進監牢——心理學家羅洛梅這麼說:「沒有一個人可能真正走進我們的私密聖堂裡。我們會孤獨的死去,沒有人能逃。這就是最深層意義的命運。」
我們都是「說故事的人」。
當代哲學泰斗麥金泰爾如此認為:「就像小說中的人物,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們的人生仍具有某種形式,向未來投射。」命運說穿了是一套與他人生命交相織的故事與地圖,或許早就在那裡了,無可更改。然而,在每一個交叉路口,我們都可以問問自己,在這個故事中自己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如何選擇才能讓故事精采好看?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最真實的「自由」。
「台客武俠」敘說如眾神降臨般身懷高貴情操的台灣小人物,與命運搏鬥的故事——而當我們敘說著別人的故事之時,其實總是敘說著我們自己。
台灣英豪,天下第一。
精采試閱
不屈劍刺竹
試合
劍尖就在眼前微微擺動——
像竹雞在草叢中挑逗般地搖動尾羽,獵食著驚懼而四處亂竄的土蜢。
這就是所謂「鶺尾」的劍術嗎?阿翔透過面罩,感受到了不知身上何處即將著劍的龐大壓力。
他代表著艋舺角頭出賽,迎戰「滅組」對手野口拓。三回合計時計點賽中,前兩回合雙方都無法有效打擊得點,形成了平手的僵局。最後五分鐘內,不管誰只要再得到一點,就可以拿到冠軍。因此,此刻阿翔眼中所有人事物都彷彿凝結,退成無關緊要的模糊背景,只剩下野口手上那微微擺動的劍尖,等待著可乘之機。
——劍由心轉。
在擔任主審的鄭大秋師父眼中,野口是逾十年來他所見過可怕的用劍高手,深得一刀流的精髓,善於利用氣勢壓制對手,技巧無懈可擊。若是用真刀,阿翔早就披傷十餘處了。
「甘巴嗲!(日:加油)」
穿著華麗和服的日本貴婦們在場邊觀戰,為俊美的少年野口歇斯底里般地尖叫著。她們多是陪伴著夫婿來台駐守的軍眷,聚在一起成立了「愛國婦人會」,從事插花沏茶等文化活動。這回,由會長,也是民政廳長夫人富子出面,邀請艋舺(今萬華)地方武術家與日本劍客一較高下。盛會難得,民眾熱烈參與,會堂擠滿了人頭,雙方加油聲震天價響。
但她們所不知的是,這場比賽對參賽雙方的男人們有不一樣的意義。年前大阪黑道組織「滅組」來台拓展砂糖業務,常與台北在地勢力發生零星衝突。官方立場當然偏袒日本人,但又怕輿論非議,激起民變,不敢公開支持。於是,滅組鬼塚老大才透過民政廳長關係,委由婦人會來安排這場名為「親善」的劍鬥,想藉機殺殺頑劣難馴的艋舺流氓之銳氣。野口拓是組中實力最高的劍手,大阪無敵。沒想到明明佔盡優勢卻久攻不下,搞得鬼塚心浮氣躁,頻頻罵道:「馬鹿!出劍!快出劍!」
「吼伊係啦!(台:給他死)」艋舺角頭老大「黑頭仔」也向場上的兒子阿翔狂吼。台灣人輸人不輸陣,打不贏也要嗆贏。聽他這麼一吼,全場佔七成以上的台灣人都齊聲附和,「吼伊係!吼伊係!」壓倒了日方的加油聲。
阿翔的表現著實可圈可點。看著他逐漸成長,沒想一下子居然能獨當一面了——若不是大秋擔任評審,他也要鼓掌叫好。自日本據台以來,禁絕中華武術傳承。這小子只能湊合著學些胡亂拼貼而來的功夫,居然擋住了日本少年高手兩回合狂風驟雨般的猛攻。雖多次著劍,阿翔憑著滑不溜丟有如鱸鰻的閃避技巧,總是讓對手的劍刃擦體而過,無法判為有效打擊才能一直僵持著。大秋心想,說來是日本人自己可笑的劍道規則反而保護了阿翔,活該勝不了。講明不能擊打護具以外部位,所以阿翔只要橫劍顧好了這些部位,適當閃避,就不致落敗。
台式劍法沒別的長處,就是守,不斷地防守;然後尋找破綻偷襲,打擊敵人弱點。這是數百年流民智慧結晶,有如鄉下植在戶外圍繞房舍的刺竹,毫不起眼,但只要有人敢越雷池一步,竹節上的倒刺保證讓他渾身披血。
若論真實搏殺本領,阿翔遠不如野口。然而,比賽就要照規則來,只要他再撐過這最後的五分鐘,就沒人能說日本人勝過台灣人,日本劍勝過中華劍!
為劍而活,不為了任何人而鬥劍——在場中對決的野口劍持中段,用劍尖繞圈,假作不經意地試探著這個矮小對手的破綻。若真刀對決,自己可輕易地在三十秒內斬斷他無護具保護的一手一腳,使之防禦崩潰。但身為劍客的榮譽感禁止他這樣做,要贏就徹底贏,贏得對手無話可說,才是野口心中最想要的。他盤算著阿翔只防守無法得點,但滿場都要阿翔贏,不出手攻擊不行;只要阿翔一攻擊,那有若荊棘的嚴密防禦網就會出現破綻!
——劍即一瞬。
只要一瞬就夠了,天才劍手野口掌握了阿翔的弱點。
在彷彿凝結的空氣中,阿翔以為毫無破綻的偷偷滑步向前,不斷地變換劍式,遮護著要害。
劍尖之間的距離不斷縮短,三尺、兩尺、一尺、四寸……
野口的劍仍然顫抖著畫圈。
是害怕了嗎?阿翔猛地跨步,揮劍橫掃。
——這是宋江陣中掃刀的招式,勢要將敵人橫腰截斷,凌厲無匹。
日本武術中這招叫啥?阿翔不知道。但那一瞬間,他看見對手雙眼射出的電光。他心知不妙,身軀下意識隨刀勢側彎傾倒,失去重心,意圖避開那道黑色的電光——
喀!
阿翔感覺到喉部護具上傳來一陣強烈衝擊。
在昏厥倒地之前,他聽到已經閃到身後的野口高聲喊出:「喉!」
再過來他眼前一陣黑暗,啥也不知了。
全場頓時陷入一片寂靜——
「刺喉!」
主審大秋驚訝只有一瞬,隨之舉旗高喊。
這是一次貨真價實的有效打擊:野口不止刺中阿翔的喉部,還喊出了擊打部位,向前進了一步,是為有「殘心」的證明。雖然大秋也想袒護台灣人,但輸了還是要認,他搖頭心想:真是可惜了,阿翔最後那一掃,露出上半身的破綻真是比桶盤還大,刺不中就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僵持了有若一輩子之久的比賽,在一瞬間分出了勝負。
野口退回線後,收劍蹲下,隨即退出場外。
輸贏明擺著,鬼塚老大與滅組的兄弟們驕傲地簇擁著野口從側門離去。
阿翔倒在場中,毫無動靜。
「他犯規!」黑頭仔大吼,「日本人犯規!」他手上一按,翻過場邊圍籬,奔向倒地的兒子。身後幾十個兄弟們也跟著推倒木柵一擁而上,只等著黑頭仔下令要打就打,要砸便砸。
日本貴婦們被這突如其來的騷亂嚇著了,蹲地互相抱成一團。負責維持秩序的持槍警察隨即進場,為首的隊長大喊:「鎮靜!」
黑頭仔急急掀去阿翔頭上的面罩,一摸頸,動脈還是有力地跳躍著,稍鬆了一口氣。他戟指向主審抗議道:「幹,對手犯規!他用腳絆倒阿翔,你眼睛是被蛤子肉糊著,沒看到是否?」
寺口幫勢力頗大,大秋不禁嚥了口口水,「大仔,日本人沒犯規。阿翔是自己要閃避劍招時跌倒。」
「黑白講你!」黑頭仔倏地站起身,幾乎和大秋鼻尖碰鼻尖,「你斟酌想看看,剛才阿翔進步時是用滑的,滑步如何跌倒?你滑給我看!」
「滑步當然不會跌倒,是閃避劍招時跌倒。」大秋耐心地解釋。
「幹!你是懂劍道否?」黑頭仔手勢招呼著要小弟們趕緊將阿翔送醫。
大秋無奈,頻頻搖頭嘆氣,「可惜!」
黑頭仔只是賽前曾草草聽過規則,知道比賽中禁止絆人。剛才從他觀賽的角度看,兩人腳步一交錯,阿翔就跌倒中劍,大有野口犯規的可能,於是就咬著這規則不放。他知道,這些日本人別的或許不在意,但損及榮譽的事鐵定不幹。阿翔傷就傷了,或許藉指控對手犯規反能得勝,不抗議白不抗議。於是又向大秋說道:「你這娶日本女人的三腳仔,良心被母狗吃去是否?若不是日本劍法規矩一大堆,這也不能打,彼也不能打,咱阿翔早就砍倒那個四腳仔。他們犯規你反而不抓,這樣敢有公平?!」
多年前日軍屠殺台灣人,因此台灣人慣稱日本人為「四腳仔」(台:禽獸),蔑稱偏袒日本人的台灣人為「三腳仔」——大秋也不是沒被這般辱罵過,堪堪強忍了下來。「黑頭大仔,這是我專業判斷,和我牽手無關,請你尊重些許。」他望著與婦人會同伴們相依著的妻子美穗,點點頭要她安心。「從我的角度看,野口一劍刺喉成功,有效擊打,他應該獲勝!全場幾百隻眼睛,也總有人看清楚吧?不信你可問你的兄弟?」
「哼!一劍刺喉?講好點到為止不傷人,現在人都昏昏去送醫急救,這款話你說得出?鄭大秋,我看你真正是不想在台北城站起?」黑頭仔撇了撇嘴,轉頭向著觀眾席大吼:「天理何在!鄉親啊,你們有沒看見日本人用腳拐倒我們台灣囝仔?」
「有!」
「日本人犯規!」
「可憐呀!」
觀眾此起彼落地大喊。
日方雖然手上有槍,但氣勢顯然就輸了一截。
「你有看到否?你有聽到否?」黑頭仔伸指戳著大秋的胸口,「你好歹生在台灣,卻不知道要為台灣人設想,你這樣對得起鄉親嗣大?對得起你自己的良心?」
良心?
前清時大秋修習過少林拳劍,日據後接觸日本劍術,他更懂得了武術是一種藝術,是一種克己的修養,超越種族的藩籬,也超越了個人的喜惡。它不問出身背景,不問師承流派,在兩方同時適用的公平規則下競技,擊中就是擊中,沒有模糊空間——大秋自問,這場的確是阿翔輸了。「黑頭大仔,我對得起我的良心。你對得起你的嗎?」
——若擔任評審者只因個人好惡而下判斷,豈非對不起武術?
日本人的槍口指著怒氣沸騰的群眾。好漢不吃眼前虧,黑頭仔不再爭辯,恨恨地向大秋倒豎拇指,轉頭就走。
素直
「我進門囉……」
當美穗拉開道場木門時,看到了空無一人的景象。「大秋,便當來了!」
大秋聽到叫喚,才從另一側的後門走進來,大汗淋漓,前襟後背一片水漬,應是才做完每日練習。「美穗,辛苦妳了。」
「不,你才辛苦……」美穗把飯包攤放在木地板上,解開藏青色的包袱巾,裡面放著三粒白色飯糰。「今天還是沒學生上門嗎?」
「嗯……」大秋拿起飯糰,三兩下就吃完一顆。
想來是著實餓了,美穗喜歡看他吃東西的氣魄。「都一個月過去,黑頭大仔也太過分,居然派小弟們站在巷口,不讓學生上道場來。簡直是要讓我們無法在此立足。」
「沒關係,正好我可以休息一陣子,好好練習劍法。」大秋脫去上衣,擦拭汗水。「身為師者,若不精進學習,會被學生趕過去。」
「是啊,但是那場比賽你又沒判錯,這樣對待我們,不是太不公平?」
「公道自在人心。我們自己做得正,對得起天地良心,不必管別人怎麼做。」大秋剝開第二顆飯糰,分給美穗。「來,『一人吃一半,感情不會散。』這台灣俗語妳沒聽過吧?呵呵。」
美穗接過飯糰,看見是有包梅子的一半,心底一陣溫暖。「大秋,鄉親如此對你,你真不在意嗎?這幾天我去菜市買菜,菜攤歐巴桑她們不賣菜給我,都說……」
「說甚麼不用理她。」大秋啃了口飯糰,「她們不賣菜給我們,妳多走幾步,到別處去買。」
「好……」另一個菜市距離這大概得走上一個小時。但自成親以來,美穗一直順著大秋,把自己當成台灣人媳婦,不管他想怎麼做都支持。「西門那裡菜色也比較多。」
低頭吃著飯糰的她,露出頸後優美的弧線。大秋心想,娶到美穗實是此生唯一的幸福。早幾年被日本人派到草山挖步道,監工的美穗父親,也就是藤澤師父,看上他勤奮努力,身手又好,常在工餘閒暇和他交流武術。後來,藤澤染上肺癆臨終前,把自己唯一愛女從日本接來,交代與大秋照顧。自那時起,兩夫妻就接下藤澤創立的道場,相依為命,至今也將近十年了。也多虧美穗的順從與支持,道場經營蒸蒸日上,大秋在日台雙方的武術界建立了一席之地。沒想到,這一場立意良善的以武會友,卻觸發禁忌般民族意識的衝突,致使生涯陷入危機。「美穗,對不起。」
「沒甚麼好對不起,你又沒做錯事。」美穗揮揮小手,「我比較擔心的是另一件事……」
「啥?」
「全台北城都說,日本人比賽犯規才贏了台灣人。連中文報都這麼寫,我怕……」
大秋驚訝,放下飯糰。「怎會這樣?」
「是黑頭仔他們……在市場、在攤販、在廟口貼告示,寫說日本人犯規,還傷了阿翔。所有經過的台灣人都在野口畫像上吐口水。他們還罵評審……說……說……」
「妳不用說了。」大秋知道自己也是被怨恨的對象,打斷她說話。「這種羞辱日本人吞不下去,一定會出事。」
「沒錯,婦人會那邊也深感不平,議論紛紛……」美穗吞吞吐吐,低頭說道:「甚至……甚至有人說要逐我出會,吊銷我們道場的執照,幸虧廳長夫人幫我說話。」
「妳委屈了。」
「啊?」美穗假作聽不懂,抬起頭,「什麼是委屈?」她微微一笑,轉移話題。「你和父親合創的劍法,都還沒使給我看過呢!」
「哈,鬧著玩的鄉下劍法可不得當真。更何況許久未練,早已忘卻大半了。」當時,中國人認為台灣人是「倭寇」,日本人當台灣人是「清奴」,兩面不是人的大秋,只有在劍術中才能找到自尊和認同,想起藤澤師父,心中一陣溫暖。
「父親不是這樣說喔……好像叫什麼……」美穗的臉上掛著少女般調皮的神情。「祕劍刺竹?」
大秋不答,仰頭大口咀嚼著又暖又酸的飯糰。
「那,我也要吃了喔。」美穗也低頭吃了起來。
夫妻對坐,相視而笑。一切盡在不言中。
此時,門外傳來一陣喊聲——
「鄭師父有在否?」
大秋起身,拉開木門,看見兩個少年仔站在街心。
「有啥貴事?」
「黑頭仔找你,麻煩你和我們走一趟。」
大秋轉頭,向倚著門邊蹙眉的美穗微微頷首。「別擔心,我馬上回來。」
風搖
「你講看看,日本人這是啥意思?」
黑頭仔把一張墨色淋漓的信紙擲在大秋腳前。
大秋彎下腰,拿起信紙細細讀了一遍。信是滅組鬼塚老大寫來的,要阿翔傷癒後與野口再比一場,時地規則由台方自訂。語氣恭謹客氣,以致充滿輕蔑之意。「我不知道這樁事。總督府嚴禁私下械鬥,鬼塚這麼做,一定有原因……」
「恁爸這一世人走踏江湖,只有我嗆人,沒有人嗆我!」黑頭仔彎腰脫下木屐,往大秋耳邊猛砸——
大秋側頭一閃,「啪!」木屐重重砸在對面的泥牆上。他可以理解黑頭仔的憤怒。要領導這麼多黑道好漢豈能示弱?
「大仔,你莫生氣。凡事以和為貴,日本人那邊我去喬(台:協調),一定可以轉圜。」
「喬啥?」黑頭仔嗆道:「你以為恁爸怕日本人?咱台灣功夫,敢會輸日本垃圾刀法?就是有你這款三腳仔,台灣人才會予人看不起。」
「想被人看得起要靠個人實力,輸就是輸,贏就是贏,和日本台灣沒關係。」大秋冷冷應道:「黑頭仔,日本人現在挑戰你別理他,阿翔若真心愛武術,好好修練,日後一定能討回來。」
「你的意思是說,咱阿翔現在拚不贏那個野口?上回日本人犯規你不抓,現在又來唱衰?」
「日本人沒有犯規。」大秋堅持,義正聲沉。
「啥!」
「你講啥小?」
「好膽再說一次!」
一旁的嘍囉們紛紛大聲咆哮。
大秋面無表情,一語不發忍受著各種難堪的辱罵。直到聲浪漸下,他才開口道:「野口比阿翔強,若是無規則真刀對決,阿翔早就死在他劍下。」
「幹,你說這種話,真正不怕死?」黑頭仔舉拳威嚇。
旁邊的小弟們紛紛抄起傢伙——扁鑽、拐棍、掃刀。
「日本人說台灣人怕死愛錢愛面子——」大秋前進一步,放鬆雙肩,直視黑頭仔的鐵拳。「我是台灣人,我怕死。」
「會怕就好。咱阿翔不怕死。」
「碰!」黑頭仔一拳揮在大秋的鼻尖。
大秋被擊得連退了三步,跌坐在地,臉上登時宛如綻裂的西瓜,青紅模糊。「希望這一拳能讓黑頭大仔您解氣……」他摀著被打斷的鼻梁,掙扎著站起身,口齒不清地說道:「真正去比的話,阿翔會死。黑頭大仔您多斟酌……」
台灣人中真懂日本劍術者寥寥無幾,以大秋之權威,如此認定兩人實力差距,黑頭仔不得不認真考量。「除非日本人自己把戰書收回去,公開道歉,否則……哼哼……」他甩甩拳頭,「否則要打就打真的,堂堂正正,像男子漢一樣對決。恁爸聽講日本古早最厲害的劍手叫宮本武藏是否?一人單挑七十六人。叫他野口也好,鬼塚也好,想挑戰,寺口幫全員應付他,好膽就來!」
宮本武藏「決戰一乘寺」以寡擊眾的故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大秋這時才明白黑頭仔想聚眾合戰,倚多為勝。這一來,勢必釀成雙方全面衝突。「日本人有槍,而且,總督府不會准許這種事發生。」
「我叫你來,就是叫你傳話給鬼塚,有角色就不要去報警察,不要帶槍。」黑頭仔說道:「恁爸也不佔他便宜,滅組有多少人全撂來不要緊。七日後天光時,馬場見,雙邊把帳算一算!」
「歹勢,講濠洨(台:唬人)這款事我不在行——」
大秋帶刺的眼神冷冷地掃過眾人身上,「大仔你請別人。」
折衝
「阿那答?」
奔走了一早上,美穗氣喘吁吁地回到家,雙頰緋紅。「大秋,事情不好——」
聽到喀喀的木屐聲,大秋才坐起身來,用濕布冷敷著仍然腫脹的鼻梁。「富子夫人不願意幫忙嗎?」
「不,她跟廳長大人講過好幾次了,但好像,廳長大人不打算管這件事。」
「喔?怎會這樣?」
「聽說是滅組鬼塚老大執意要這麼做。他說這番寺口幫做得太過分,日本人明明贏了,卻被說成沒榮譽感,損及武士道精神,廳長大人非常不滿,要給台灣人一個教訓。」
「真糟糕,那可否請富子夫人親自去和鬼塚老大談?請他收回挑戰書,化干戈為玉帛?」
「她去過了,」美穗幫大秋換了條濕布,「鬼塚老大堅持要和黑頭仔那邊見輸贏——他大概認為滅組穩贏。依野口的劍術,台北城無人能勝;寺口幫若要倚多為勝,他也不怕,他調得到火槍——這正是滅組壓制寺口幫的好機會,他不會放過的。」
「唔……」大秋陷入沉思。
聽著戶外竹叢被風吹過的沙沙聲,兩人相對不語、苦思對策。
「大秋,」美穗問道:「男人們為了武術、為了名譽、為了地位、為了權力而戰鬥,真可以連生命都拋棄嗎?」
「對鬼塚、黑頭仔他們來說,是的。」
「唉,那我看要他們停手,恐怕真的要宮本武藏復生,打得他們服服貼貼的才行了……」美穗嘆氣。
大秋取下濕布,仰頭說道:「我正在想這件事。」
夫妻心有靈犀。
美穗大驚,「你難道是想……」
「嗯!」大秋對美穗猛點頭。「美穗,支持我,讓我試試看!」
「我不要你做這麼危險的事!」美穗怒道:「你自信能贏得過野口嗎?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野口可是在大阪黑道中真刀真槍浴血得來的劍術,和你在道場中用竹刀練習完全不同,你可是會死的呀!他們要鬥,就讓他們去鬥,你沒有理由去蹚這趟渾水。難道你想出名?爭台北城最強的名號?」
大秋沉默片刻,續道:「我?不是的。想要出名,沒理由當個老師。」
「那你『壞鬥』(英文日語發音:fight)什麼?」這個新的外來語,美穗也是剛學會。在台灣,這正是充滿生氣、向上奮鬥的時代。
「這是我少年時抗日留下的,那時我想守護我的國家,所以我戰鬥——」大秋捲起衣袖,輕撫著上臂一條有如蜈蚣般的醜惡傷口。「後來我發現,不管誰來統治台灣,家鄉都沒有改變,美好的還是美好,醜惡的還是醜惡。我才知道『愛國』是個虛假的目標。所以我退讓了,我投降了。」他看著美穗清澈的雙眼。「日本人、台灣人、中國人……這種事,那是假的分別,無聊的分別。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身邊活生生的人,每一條生命都同樣可貴,我要守護他們,那就是我戰鬥的理由。」
「可是你守護的人不見得領情啊,你看他們把你打成這樣!」美穗憤憤不平。「台灣人說你是日本人,日本人卻不承認。我們何苦來哉?」
窗外,一條瘦得只剩皮包骨的黃狗走過,在屋角嗅了嗅,懶懶地抬起腿,悉悉哩哩——
「喏,妳看!」大秋笑了,指著屋外的竹叢,說道:「那叫刺竹,節節是刺,又醜又怪,連狗都想在它身上灑尿。可是它守護著我們的家,宵小看到就皮皮挫(台:害怕顫抖)。它每天這樣做,時時這樣做,它有要我們領情嗎?」
「我不准你去!」美穗不想再和他說下去,起身去做午飯。「你不為自己著想,也要為我著想——這事沒得商量。你敢去就離緣(台:離婚)!」
大秋無奈,對著隨風搖曳的竹叢,喃喃唸著來台先賢的詩句——
「惡竹參差透碧霄,叢生如棘任風搖;那堪節節都生刺,把臂林間血已漂。」
嗆聲
吃過晚餐,說是要讓美穗再去拜訪一次富子夫人,大秋把她哄著出門去了。
他把碗筷桌椅都收拾好,端坐細細回憶了幾次劍法,才提著竹刀走上路燈忽明忽滅的北門街。
滅組的長屋外,掛著黑底紅字的大燈籠,門內傳來男人們喝酒叫囂聲,暑氣如蒸。
「失禮了!」
大秋在門外高喊一聲,刷地拉開紙門。
屋內約有十幾個男人,笑鬧著似乎在準備明早與寺口幫的決戰。有人正在擦拭著火槍,有人正在整理盔甲。原本熱烈的氣氛被大秋這麼一打擾,剎時冷卻了下來。
「你想做啥?」鬼塚老大坐在地爐前喝湯,頗不耐煩地問道。
「很抱歉,冒昧打擾,我就開門見山直說了。」大秋彎腰九十度,照日本人的儀節,向鬼塚深深鞠躬。「能否請滅組收回挑戰,取消與寺口幫的決戰!」
「哈哈!」鬼塚老大聽見這微不足道小人物可笑的提議,差點打翻手上湯碗,他早已忘記大秋是劍道賽當日的裁判,「你以為你是誰?說取消就取消?看你手上提劍,應該也是懂劍道的人,難道不知劍客的名譽就是生命?」
日本取得史上第一塊殖民地,黑道豈能缺席?鬼塚是大阪滅組的副會長,幫中的第二號人物,啣命來台開拓地盤。而野口拓是會長之子,豈能讓他折了威風?若在台北就遇到麻煩而退縮,以後就沒得混了。
「我知道。但還是請老大您打消決鬥的念頭吧!」大秋仍然保持著彎腰的姿勢。「野口的劍術雖好,但台灣人這邊也有厲害招數,他贏不了。那天比試,阿翔是故意讓他的……」迫不得已,他只好說一次謊話了。
甫聞此言,鬼塚老大的下巴都差點掉下來。他瞥了下坐在屋角整理刀具的野口,野口倒是蠻不在乎地聳聳肩。「啥厲害招數?我怎沒感覺到?是被砍斷手腳也沒感覺的那種嗎?」
哄堂大笑。
大秋還是沒有直起腰,恭敬說道:「祕劍刺竹,您聽說過嗎?」
聽到如此荒謬的回應,鬼塚老大反而笑不出來。「沒聽過!」
大秋從懷中取出整齊疊好的書信。「那在下謹此正式向滅組遞出挑戰書,夜明之前,也是與艋舺合戰前一小時,我在馬場恭候野口桑,一對一真劍對決,無規則一分勝負。」
鬼塚接過挑戰書,看也不看就揉成一團,丟進地爐。「哼!你算甚麼角色?」
信紙隨即起火燃燒,大秋說道:「挑戰書剛才經過市場時,我已張貼在告示木牌上。如果滅組不敢應戰,就代表認輸,承認劍術不如台灣人。那麼艋舺方面就不必要出戰了。」
「你……」鬼塚氣得說不出話。
想死嗎?在黑道拚殺這麼久,野口知道,敢對他當面嗆聲的只有兩種人:全然不知劍為何物的白痴;或正好相反。
——大秋看起來不像白痴。
他斜眼瞥了大秋一眼,拾起長刀,默默地鎖著刀釘。
一閃
黑夜將盡,馬場町上一片寂靜,枯黃的荒草上泛著一片新月微光。
——此處約為今日萬華區南部濱新店溪,設有練兵場,供士兵操練與騎馬,後來亦作機場使用。河堤邊曾為刑場,冤魂無數,今設「馬場町紀念公園」。
其當時,野口的劍尖在大秋眼前微微擺動。
鶺尾般的挑逗劍術帶給大秋不知身上何處即將著劍的龐大壓力。
大秋身上的藍布短衫已有七八道破綻,大腿後背上都滲出血跡。然而,這些都是膚淺的皮肉傷,不礙事。
他手上的竹劍依然斜斜朝天矗立著,擺出了防守的姿態。
野口一出劍,他就勉力辨清刀影來勢,將竹劍往鋼刀的側腹去撥,然後借竹劍本身反彈之力,順勢向前擊打野口握劍的手臂。
縱被偏離目標的刀尖劃中也要忍耐,就這麼堅持了將近三刻鐘。
祕劍刺竹,絕不屈服!
——對手揮劍的動作越大,竹劍可以擊打的空隙就越大。
——對手越加強出劍勁道,竹劍反彈的力道也越強。
——對手出劍越快,握劍的手臂就越會感到酸痛。
——對手就像走入刺竹林中,揮灑不開,動彈不得。
漸漸地,鶺尾已經不再靈活躍動,宛如得瘟的竹雞。
野口悄悄地交換握劍的雙手,左手貼著護手;右手酸麻不已,只好虛握劍柄尾部扶著。
一換手執劍,威力頓減。
這一來,他身體右半側毫無掩蔽。
是時候了……大秋把握住逆襲之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抖腕揮劍。
劍光一閃——
「啪搭!」竹劍正中野口的右頸與肩膊交接處。
——若換作鋼刀,這一記「左袈裟斬」已經將野口一分兩半了。
遭此猛烈一擊,野口大動脈瞬間閉鎖,神經受到劇烈震盪,失去知覺,轟然倒地。
劍鬥出乎意外地結束,旁觀諸人目瞪口呆。
新店溪水潺潺聲傳來,使這鬼氣森森的河岸顯得更加寂靜。
「可惡呀!」
過了片刻,滅組的兄弟們才紛紛舉起刀槍,作勢欲撲。
大秋拄劍喘息,斜睨著鬼塚老大,「這就是武士道精神?」
鬼塚嘶嘶吸著暗冷夜氣,平息激憤的情緒。「哼,祕劍刺竹?」漸漸地,他放鬆了緊繃的肩頭。「一勝一負,日本武士沒有輸給清奴;日本劍道也沒有輸給中國劍術……」
「僥倖,只是僥倖——日本劍有日本劍的優點,中國劍有中國劍的優點,台灣劍法只是把兩者融合罷了,沒啥了不起。」大秋也不為己甚,說道: 「什麼中國人日本人的仇恨,與台灣人完全無關。我們只想好好過自己的日子。把那些無聊的恩怨放下,走開吧,鬼塚老大……」
「走!」鬼塚老大頭一撇,引著手下退走,將敗將野口棄於馬場,身影沒入夜色中。
休憩片刻,於黎明曙光乍現之時——
大秋肩頭扛著昏迷的野口走入艋舺街道,把旭日拋於身後,影子筆直地在他身前拉開,無比的巨大。正在告示牌前議論紛紛的鄉親們停下手邊工作,無言地注視著這不可思議的景象。
原本抱著必死的決心,帶著五六十個兄弟正要出發的黑頭仔放下了掃刀,蹲在街邊豎起了大拇指,喝道:「幹,算你有角色!」
然而此刻,大秋心裡只想著一個人,街上的人群擾嚷,他視若無睹。
他想回家,加緊了腳步,毅然前行。
「阿那答……」美穗四處遍尋丈夫,擔心了整夜。一見良人歸來,忍不住嗚嗚啜泣。
「我回來了!」大秋把軟綿綿的野口放在屋外長凳上,傲然挺立在妻子的面前,側腰、大腿上的劍傷仍淌出血來。
「你……你看你……全身都是傷……」美穗手忙腳亂,猛翻著五斗櫃,抽出一捆潔白的紗布。
「對不起,讓妳擔心了!」大秋猛地向前,抓過繃帶棄於地上。
夫妻相擁,皆流下歡喜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