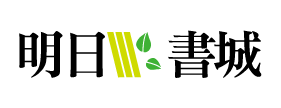會員登入
我要找書

-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推薦
- 目錄
- 內容試閱
特色
第七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首獎
講太完美的故事,會得到報應
──燦爛天才 徐行 橫空出手
簡介
駱以軍:「被作者那噴著光燄的天才所征服!」
喬靖夫‧甘耀明‧果子離‧施達樂‧陳夏民‧楊富閔 感動推薦
盜跖的狗註定要對著堯吠叫,一旦有了真正重要的東西,就註定了這輩子要像狗一樣惶惶追趕,猶恐失之。
這不是他們要的結局,可是他們誰也無能為力。
狗子手中長劍雷霆一般奔向嘉義。劍光流轉中,嘉義手中單刀寒光閃爍,飛快地揮舞著和狗子展開一場惡戰。
暴雨落在平湖之中。
蓮花在一瞬之間綻放和凋零。
漣漪向四周盪開,激起凌亂的波紋,血的漣漪開始擴散,誰都不能回頭了。
如果還拿他當自己人,就要殺了他!
爺爺說,你這不是拿他當兄弟。
狗子說你不是我兄弟。
所有的聲音在嘉義腦中響起,一遍一遍,越來越響,在內心的一片譁然中,嘉義終於聽見了自己的聲音……
台灣人。
剩下的,讓故事說。
剩下的,讓故事說。
十一、鷓鴣斑
十二、回天
十三、飛蓬
十四、雙連環
十五、解
十二、回天
十三、飛蓬
十四、雙連環
十五、解
作者自序
那只是一個故事
人是為了什麼要說故事?
是謊言的預演還是推理的訓練?
為了解釋什麼?或是掩蓋什麼?
人類的第一個故事會是什麼樣子呢?一個衣不蔽體的野人站在一地殘缺的腳印中央,他就看見了一群人獸的爭鬥,這個腳印覆在那個之上、什麼被追獵、什麼翻滾撲捉,然後他要決定是要趕快逃走,以防掠食獸仍在附近,還是循著腳印去找那負傷逃脫了的同伴。他不知道這些事是不是真的發生過,一切只在他的腦中,那只是一個故事。
或者一個人在深夜裡無意中仰望星空,看見千萬光年之外一顆星星熄滅了,為此驚慌不已。為什麼光會消失?如果所有發光之物終將黯淡,那麼每天早上照耀大地的太陽是不是也有這一天?是不是所有的光明終將消逝於黑暗之中?他用雙手環抱自己,感到心底有某種可怕的東西慢慢爬上來,但當時「孤獨」這個字眼還沒被發明出來,因此他對此無話可說。於是他對自己說了一個故事,在遠得看不見的天空之上,有一片草原,星星就是這片草原上的繁花,像地上的花朵一樣,今天摘下了,明天又會再長出來。一個溫柔的愛人摘去了一朵,明天、天空的草原裡還會有新的花綻放。如此他就不再去想為什麼光明終將消逝,和明天升起的太陽是不是終有一天會熄滅,這些對他而言不但不重要而且很危險的事,畢竟在他進行哲學思考的時候,很有可能後面有隻尖牙利齒的肉食動物正在列菜單。
那只是一個故事,而且沒錯,我們的太陽也只是一顆終將熄滅的星星。
故事張開了一張網,把所有不確定和迷惘都隔絕在外,溫柔包覆,使人不致墜落。
也很有可能、第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寒冷的山洞中、垂死的孩子和心碎的母親。母親看出了孩子很害怕,便對他說:明天,我們會到樹林裡去採最甜的莓果、在發亮的小溪中飲水、在微風輕拂的草原上撲捉飛蟲……明天、等到你好起來的時候。
母親知道她留不下這個孩子,但還是在他耳邊不斷地輕聲說話、說那些不管他們多麼渴望也不會實現的小事,而那終究只是一個故事。
為什麼人要說這些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或心知永遠不會成真的事?
為了解釋什麼或是掩飾什麼?
英文的story源自希臘文的historia,原意是探尋、調查。
愛因斯坦利用思維實驗假想自己在宇宙中追逐一道光,這是狹義相對論的起點。故事有的時候是理論工具,所有的假說在被驗證前都只是故事,故事就是我們探尋真相的探針,刺探現實的各種可能性,但故事真正的意義卻不在尋找答案,解決問題,而是製造問題,惟恐天下不亂地提出各種可能,製造額外的、絕大多數不必要的資訊,然後、其中也許有那麼一點真實,但故事並不在乎。
醫生也許必須對所有症狀都有明確迅速的解釋,可是故事並不想解決或治癒任何東西、故事容許迷失。
故事並不總是幫助人,有些人相信如果說了一個太好的故事,是會招來報應的。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語》在序裡寫道:「羅子撰水滸。而三世生唖児。紫媛著源語。而一旦堕悪趣者。蓋為業所偪耳。」
宣鼎在《夜雨秋燈錄》自序中說,因為在冬天看見了蝴蝶,因此設壇扶乩,呈上自己的文章,乩仙告訴他他的前世是一個道士,「以弄筆頭獲過,今又弄筆耶?」
即使如此,人還是不斷說著故事。
人是為了什麼說故事?動物也許會用聲音和姿態欺騙掠食者,也許會說謊,但所有動物中,只有人類會說故事並且為故事沉迷。
故事是謊言的預演嗎?或者僅是人類大腦演化出推理能力時生出的副產品?就像嬰兒的囟門,因為人類的腦部越來越大,為了順利通過產道,只好設定了一個未癒合的腦殼,不限制腦部的發育,但也使人類的新生兒比其他動物都要更脆弱。故事解除了人思想的限制,卻也有時讓人脆弱、使人迷惑。
在故事中可以實現現實中不能成真的一切,但故事的意義並不是從現實中逃開,現實並沒有那樣可憎,非得逃避不可,只是它總是靠得太近遮蔽了所有的可能性,但只要有一個瞬間,人的心念可以被故事所吸引,就能暫時離開現實,然後看見現實的另外一種樣貌。
現實會欺騙人,但故事真誠地說:這只是一個故事。
故事並不指導人、拯救人、幫助人、它甚至不安慰人,可是它讓人思考,並且不拒絕一切看法。現實強迫人形成看法,可是故事並不在意人的看法,你可以以所有的角度去看它甚至可以毫無看法地任由它流過,故事是冬天的蝴蝶,冬天裡沒有食物也沒有同伴,冬天的蝴蝶沒有任何目的地生存,它唯一的意義,不過是打破「冬天沒有蝴蝶」這個限制,不為什麼地。
我也不為什麼地去讀故事,然後覺得「這樣好像會很有趣」,就說了一個故事。如果有人能夠覺得有點有趣,有那麼一個瞬間,可以吸引某人的心思,那再好不過。
只有人會說故事、只有人會被故事吸引,即使明知不是真的,只是一個故事。
我說了一個故事,並不為欺騙,或者解釋什麼、治癒什麼,我的探尋並不追求答案,我的謊言並不冀望成真,我只是一個沉迷於故事的人。
如果故事是謊言,那麼我說謊成性、如果故事是掩飾,那麼我恆久沉默。
我沒什麼可說的,所以我讓故事說。
精采試閱
十一、鷓鴣斑
1
「奇怪了?沒有那麼深啊……」狗子皺著眉,用手指輕輕觸摸頭上那個鐵鐧砸出的傷口,些微的刺痛使他嘶嘶地吸著涼氣。
他悄悄回到住處,換下滿是血汙的衣服,自己把血衣劍所傷的傷口都處理好,開始檢查頭上的傷口。給砸上一鐧後他就一直感到噁心暈眩,腦袋生疼,耳中嗡嗡直響,還以為開了多大的口子,沒想到表面的傷口卻很小,現在已經不流血了。
狗子下午就開始在江梓儀面前裝病,老喊頭昏腦熱的,說怕是傷了風,傳給少爺就不好了,天沒黑就關進自己房裡,託隔壁的楊大嬸給少爺準備晚飯,燒一大壺茶,留下一碟子消夜。少爺也怕下考場前染上傷風,叫狗子快快進房歇著,別在外面亂轉,沒有人知道狗子在夜裡悄悄出了一趟門。
血衣劍留下的傷口都是皮肉傷,只有左肩上一道口子稍深,只要不刻意使力倒也沒有大礙。
回來的時候他多繞了好幾圈,確定身後沒有人跟蹤,至少現在是安全的。四城門應該都把住了吧?就這樣像平常一樣上街買菜,照顧少爺一日三餐,過些日子城門把守鬆下來了,就快快帶著天奪出城遠走高飛——
這傻少爺家裡大概也要發現不對勁了,等到來水鄉江家來人,他這一路說的瞎話就要穿了。
計畫大體是成功了一半,他拿到天奪,也從李大人府中脫了身,可是他卻沒辦法覺得是成功的。李萱兒死在他手裡,而他沒有給過她任何機會。
「狗子!」
江梓儀站在門外喊了他一聲,他嚇得趕緊縮進被子裡,把頭用被子蒙著應了一聲:「少爺……」
「狗子,你先用被子把自己蒙上,我再進去。」江梓儀提心吊膽地說。
「少爺,你別進來!我怕——」
「我進去啦!」
狗子想出言阻止,江梓儀就推開門進來了。
「吶,這消夜……我今晚不想吃,你都吃了吧!放到明天要餿了。」江梓儀手上拿著一盤桂花糕。
「少爺,我不餓……」狗子一心只想打發少爺出去,趕緊說。雖說晚上已經涼快些了,這麼熱的天讓他摀在被子裡可真吃不消。
「楊大嬸說你晚飯都沒怎麼吃,說不餓是騙人的吧?反正你得給我吃了,我都拿進來了。」江梓儀不由分說地把碟子放在桌上。
「謝謝少爺……」狗子怕這病裝得不像,給楊大嬸看出手腳來,晚飯沒敢多吃,偏偏這會兒正頭暈犯噁心,一點也吃不下,可這傻少爺平時只會抱怨,今天竟然給他送消夜來,狗子不由得心中一動。
「別謝我!你快點給我好起來!好了就別讓楊大嬸上我們這來了,她一來盡想著要給我作媒,好像全天下沒成親的都歸她管似的!」江梓儀皺著眉頭埋怨著,又說:「對了,我這有一封信,你如果明天好起來了,就給我送去給李小姐……如果沒好,你可別去,要是讓李小姐染上傷風可就太罪過了!」
江梓儀說著從懷中掏出一封信放在桌上。他又給小姐寫了首詩,急著要給小姐送去,心裡還想著小姐接到這信,要露出怎麼樣嬌羞可愛的表情呢。
「狗子,你頭怎麼破啦?」江梓儀突然看見狗子頭上有個傷口,便問道。
「這個啊……」狗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頭上的傷口說:「我頭有些發暈,不小心跌了一跤……」
「狗子……你這真的只是傷風嗎?」
糟糕!難不成我哪裡露出破綻了?怎麼會給這傻少爺看了出來……狗子聽少爺這麼說,心中一驚,強作鎮定道:「是傷風了,我昨兒個夜裡睡覺沒蓋住肚臍——」
「你別裝蒜!」
江梓儀這麼一說,狗子在被子裡抓住了天奪的劍柄。如果這事真穿了,恐怕得要連夜逃走,他不能讓少爺去報官。
「我聽見你吐了……該不會是什麼比傷風更嚴重的病吧?」江梓儀皺著眉說。
「少爺……傷風上吐下瀉也是有的,您別擔心,明天我就好了……」狗子鬆了一口氣,小聲地說。
「不行!萬一真的是什麼大病,一拖就壞事了!我還是讓楊大叔給你叫大夫吧!」江梓儀說著轉身就要往外走。
「少爺!我真的沒事……」狗子見江梓儀往外走,嚇得一骨碌坐起來,伸出手來亂揮著要他回來。
江梓儀回頭看見狗子光著臂膀揮舞著右手,兩條腿也光溜溜地伸出被子就要下床,急得大叫:「你、你這……成何體統!」江梓儀從小養在深宅大院裡,又沒有兄弟姊妹,長這麼大還沒看過自己以外的人光著身子,看見狗子這副德性臉都綠了。要開葷也該在煙花柳巷、溫香軟玉的花姑娘房裡,他可不想在這臭烘烘的屋子裡看這傻小子光屁股。
狗子這才低頭看見自己光著膀子,趕緊又縮回被子裡小聲地說:「我……我熱嘛……」他剛剛給自己紮傷口,還來不及把外衣穿上,江梓儀就來了,這下他既不能出去追他,又不能讓他去找大夫,急得他滿頭是汗。
「還說不是大病!你給我乖乖躺下!我得叫大夫來……」江梓儀心想他一定是發燒了,但又不敢去摸他,確認他是不是身上發熱,見他一頭汗水,為防萬一還是該叫大夫來一趟。
狗子知道城中出了大案,有人受傷,衙門一定第一個先找城裡的大夫,要請來了大夫這事就要穿了,心裡著急,但還是耐著性子拿話哄少爺:「少爺,我真的沒事啊!你別去,我叔叔說了,半夜裡能請得來的都是醫死人不償命的江湖郎中,除非到了死馬當活馬醫的時候,千萬別半夜請大夫,您要真請來,非把我治死不可……」狗子哭喪著臉說。
「這……」江梓儀一向不管事,遇上這事也不知該怎麼辦,聽狗子這麼一說還真信了,收住了腳沒往外踏,猶疑地看著狗子。
「少爺,您讓我睡一夜就會好了,我是福薄命賤壽算長,輕易死不了!要不,明早還下不來床,您再找大夫不遲……」
狗子好說歹說總算把江梓儀哄住了,少爺回房睡下,他才精疲力盡地躺下,卻怎麼也闔不了眼。
雖然少爺不敢靠近他,要進房還要他先把自己蒙在被子裡,可是這傻少爺是真的心疼他。如果少爺知道他今天幹了什麼好事,他一定會恨他的。
他不想傷人性命,可是今天在那座小院裡死了四個人。
一開始就該殺了李皆雲的,是我的一念之仁殺了他們。
「你要夠狠才能行好……」記憶中一個含糊的聲音說。
會變成這樣,難道都是因為我不夠狠嗎?可是當我狠下心來,我還能心好嗎?一開始要我狠下心的好心又該怎麼辦呢?
頭痛和暈眩還沒退去,他的思緒開始渙散,血衣劍的眼睛、小姐的鮮血、李蒔言溫順又陰險的笑臉,一切都被攪碎散佈在他的半夢半醒之中,既無法入睡又不能醒來,既無法忘記,卻也不能清楚地想起。
快睡!狗子命令自己:天亮的時候我就得好起來。
2
薛捕頭領著老焦和姚三在李大人的書房中勘察,李大人另有公事不在府中,這倒稱了薛青原的意,他一點也不想見到李大人。
薛捕頭的右臂上了夾板,腰間掛著他的流星飛抓,飛抓的五個爪折了兩根,但他失去的遠比這個多太多了。
小金腿給砸佘了,還在家躺著,肥牛和竿子都給他叫去把城門,他只帶了兩個人回到這座宅子。
裝天奪的匣子還敞著擱在書案上,匣內空空如也,匣底襯著黑綢,薛捕頭過去把那匣子翻來覆去地看了好幾遍,匣底是好的,兩旁也沒有機關,要開匣子只有掀開蓋,可要開蓋子不開鎖頭不撕封條是不可能的,薛捕頭仔細察看了匣子上殘留的封條,這封條是李大人親自撕的,在天奪遭竊之後。
封條用的紙極薄,就算用蒸汽蒸軟揭下來也不太可能完整無缺地貼回去。鎖頭的鑰匙李大人貼身保管,封條也是李大人親手所寫,隨寫隨貼沒有備份,除了李大人之外,沒有人可以打開這個匣子拿走天奪。
可是天奪確實被盜走了,薛捕頭絕不相信什麼狐祟,可他怎麼也想不明白那賊怎麼能偷走天奪,難道真有隔空取物的手段不成?
「薛捕頭,辛苦辛苦!」李蒔言踏進書房,笑著對薛捕頭抱拳拱手。
「少爺言重了,卑職職責所在,盡職而已。」薛捕頭冷冷地說。
「薛捕頭此番偵查,可發現什麼可疑之處沒有?」
「可疑之處沒有,可疑之人倒有。」
「喔?此話怎講?」
「少爺,你也別裝蒜了,李大人若真想要天奪回來,就得實話實說,你們連我都信不過,我要怎麼幫你們找回天奪?」薛捕頭打一開始就沒信過李大人,但天奪被盜是真,只是關於天奪從何處被盜,恐怕是騙人的。
一定是那老畜牲怕我也圖他那鬼劍,所以做出把天奪藏在匣子裡的表相,真的天奪恐怕藏在書房某處,只是不在匣中,李大人一進書房就發現天奪被盜,開匣只是做樣子來哄老子的,不這樣想就不能解釋犯人如何能不壞封緘盜走天奪。
「實話實說?您這是讓我從何說起……」李蒔言苦笑著說。
「哼,天奪打一開始就不在這個匣子裡吧?就從天奪是從何處被盜說起如何?」
「你是說天奪被從書房盜走是我們作的一場戲囉?」李蒔言笑了起來:「眼見非真,耳聞是虛,不愧是薛捕頭,連報案的也信不過,只可惜你這份聰明用錯地方了。」
「你是說李大人沒有事瞞著我嗎?」薛捕頭額角浮現青筋,他強壓下滿腔怒火,才沒對著李蒔言吼出「你他娘的再給老子裝相,老子扒了你的人皮」。
「薛捕頭,我不是說你說的沒有道理,可我義父有可能,卻沒有理由騙你。」李蒔言心平氣和地說:「我義父若要瞞你,一開始就不會把收到書信告知要盜天奪的事對衙門裡說,況且若真有什麼需要保密的事讓你知道了,也不打緊,衙門的人也是『自己人』,沒有什麼好顧忌的。」
薛捕頭聽到他說「自己人」,受傷的手臂和右胸一陣疼痛,才發現自己忍不住握緊了拳頭。
李蒔言話說得客氣,但他知道這是說若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李大人也不屑瞞他,他薛捕頭不過就是官府的走狗,李大人招招手就得乖乖過來,不需要時一腳踢開就是,李大人要他閉嘴方法多得是,犯不著演這齣戲哄他。
「薛捕頭,您還是別在我們身上費心,衙門的人也不見得靠得住呀……」李蒔言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三個官差都悄悄咬住了牙根。
薛捕頭一聽他這話火往上衝,差點就過去跟他動手,可他知道李蒔言不是好惹的,現在的他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況且他說的也不全是瞎話,二愣子就是那女賊的眼線,幫那女賊逃了,他不能說他手下人都沒有問題。
薛捕頭生平第一次受這樣說不清道不明的窩囊氣,他一向只信任他看中的人,只看得上他信得過的人,可這次他手下人裡出了奸細,他唯一能信的卻偏偏只有李大人這他怎麼看都看不上眼的狗官。雖然李蒔言的話很不中聽,可他說得沒錯,李大人沒有理由騙他。
「薛捕頭,請您放心,府中裡裡外外我都交代過了,您要問話所有人一定全力配合, 希望你早日查明真相,追回天奪,只是另外那件事,也要請您多多幫忙,您可要好自為之啊……照我說呢,少輸為贏,您是聰明人,想必知道該怎麼辦。」
李蒔言溫文有禮地說完便退出房中,薛捕頭氣得渾身顫抖,好半天才說得出話來:「老焦、姚三!你們給我記著,老何和二愣子死得太不值了,從今往後,我要再叫你們豁命幹,你們就只管抗命好了,就聯手宰了我跟上頭說我殉職了,我絕不怨你們……」
「頭兒……你別這麼說……」姚三聽他這麼一說眼眶就紅了,他那天才跟二愣子說「再這麼愣往下瞎撞,遲早有天撞進墳坑裡去」,沒成想就真出了事,他心裡這疙瘩堵得他難受極了。
在一旁的老焦也低下頭來不說話,他年紀大了,腿腳也不如其他人利索,但薛捕頭就是敬他穩重,沉得住氣,才處處倚重他,他可不能在這時候動搖。他和老何是鄰居,兩代的交情,可他連李蒔言說他們的人靠不住他都一聲不吭地忍了,他知道薛捕頭帶他們來,是因為姚三會察言觀色,而他向來穩重,知道他們兩個不會添亂,他就更不能在這時候拆薛捕頭的台。
薛捕頭領著姚三和老焦出了大門,正好看見狗子在外牆踅磨,狗子和薛捕頭一打照面就不自覺地縮起脖子,轉過臉去,薛捕頭大喝一聲:「站住!」
狗子屏住氣不敢逃走,他賭的就是薛捕頭沒認出他來。
他今早在灶下生火時故意夾了一把濕柴,弄得滿屋子煙,少爺抱怨個沒完,他也一頭一臉的煤灰,他頭上的傷很小,給煤灰一遮,不仔細看不出。
早上上長遂家一趟,和她約好了留隻雞,過幾天給少爺熬湯,說是少爺這陣子心神不寧,有些氣虛,想弄個老母雞給少爺補身子。長遂見狗子一頭的灰,老實不客氣地笑他怎麼搞得跟炭窯裡撿出來一樣,還擰了手巾要給他擦,沈大娘也直說他這麼在街上晃太不像樣,還幫著打水給他洗,他趕緊推說有要事,逃了出來。他們都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異狀,現在就看薛捕頭買不買帳了。
「小兄弟,」薛捕頭左手按住狗子的肩頭:「又給你家少爺送信啊?」
「是……」狗子低下頭畏畏縮縮地說:「可瑞雲姊早該出來給小姐買花啦……怎麼……今天……」他越說越小聲,頭低得幾乎要縮回腔子裡去。
姚三見他還不知府裡出了事,正要說,薛捕頭抬起手來截住他的話,不懷好意地對狗子說:「小子,你真是來送信的?把信拿出來我看看!」
「大爺……這——」
「還是我去找你們少爺,問問他信裡寫了些什麼……」
「慢、慢!大爺,我給您瞧就是了,您可是說過不管這事的,我們家少爺也都規規矩矩,除了遞信送詩扇,再沒別的了……」狗子為難地苦著臉,一邊說一邊把髒手在衣服上擦了好幾下,才小心翼翼地用兩根指頭捏住一角,從懷裡拿出一封信。
薛捕頭粗魯地一把抓住信封,一看封面的確是那天看到的江公子的字跡,這小子所言不假,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半句瞎話。
「小子,這麼熱的天辛苦你跑這趟啦!我請你喝茶!」
「大爺!冤枉啊!」狗子一聽嚇得臉色大變,立刻嚷了起來:「我、我什麼也沒做……別抓我進班房!少爺還等著我帶回信呢!」
「誰說要抓你啦!」薛捕頭手裡抓著信,一個爆栗敲在狗子頭上,正好敲他頭上的傷處,痛得他一個踉蹌差點沒跪下,一夥官差看了都暗想:真是個沒用的小子,敲一下就站不住腳。
薛捕頭皺著眉道:「我是說到那邊的茶棚喝杯茶!你冤枉個屁!瞧你這賊膽如鼠的窩囊勁!」
狗子扶著腦袋一面哈腰一面道:「是、是!大爺費心了!」
薛捕頭領頭,老焦和姚三一左一右挾著狗子,進了茶棚落了坐,薛捕頭一把撕開狗子帶來的信。
「啊……」狗子一急伸手想要攔,叫了一聲,見薛捕頭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後半截話都硬生生吞了回去,只敢縮在老焦和姚三兩人中間小媳婦一樣,把頭低得緊緊的,真比老鼠見了貓還乖順。
江梓儀在燈下掛著傻笑寫這信時,心裡想的是李小姐含羞帶怯地用雪白的柔荑輕輕展信,可沒想到會是這幾個凶神惡煞的大老粗一把撕了信封,抖開信紙,皺著眉頭大剌剌地在茶棚裡看他的信。
「哼!又是什麼『喜獲釋憂語更添相思苦』!不是志在大比嗎?怎麼成天盡琢磨這個!」薛捕頭煩躁地說,他這會兒正是瞅什麼都不順溜,抓著信紙一把拍在滿是茶漬餅屑的桌上,狗子只能苦著臉坐在一旁不敢吱聲。
「小子!」薛捕頭瞪著狗子沉聲道。
「大爺……」狗子唯唯諾諾地應了一聲,手悄悄地伸到桌子底下。
若是有什麼一差二錯的,給薛捕頭看出不對來,他就要桌子一掀,打翻兩個差人奪路逃走,他雖然手無寸鐵,但要打他們個出其不意還是有勝算。
「我問你話你可得老實說,我們在這裡請你喝茶是客氣,要進了班房,茶就沒這麼好喝了!」
「大爺面前我怎麼敢說瞎話?自然是大爺問什麼我說什麼,大爺不問什麼我也都說、都說、說個底朝天!半點不帶存著的——」
「混蛋!你當這是倒賣雜貨鋪呀!」薛捕頭不耐煩他多嘴,罵了一句打斷他的話,這才說:「你給我說說,你給你家少爺遞信多久了?」
「這……從上回做廟會那時……也有一個月多了……」
「每次都是瑞雲接你進去的嗎?」
「是……」
「進府還見了誰?」
「見了、見了小姐……還有……還有很多漂亮的姊姊……瑞雲姊姊給指引過幾個,可我忘了……」
薛捕頭眉頭一皺,姚三最會見風使舵,一見頭兒臉色一沉,立刻一巴掌打在狗子後腦杓上罵道:「誰問你漂亮姊姊啦!你這小王八!給我好好說!不然爺抓進去吃幾天免錢的飯菜!大嘴巴子賞你!」
狗子哭喪著臉委屈地說:「你們讓我老實說的不是……」
「你還多嘴!」姚三瞪起眼睛來手又抬高了要搧下去,薛捕頭下巴一撇,姚三才住了手。
「我問你,你遞信時除了小姐住那院還去了哪裡?」薛捕頭繼續問道。
「就去小姐那院我就快沒命了,還想我去哪裡……」狗子上回給薛捕頭逮住過一回,可給整得夠嗆,他說起來一肚子委屈,聲音還帶著哭腔。
「你小子是活膩味了不成?找揍啊?」姚三在一旁惡聲惡氣地說。
狗子不理姚三,抬頭可憐兮兮地看著薛捕頭,一副快哭出來的表情說:「大爺,您不是說不管我家少爺的事嗎?您問這些是……是要拿我們家少爺……怎麼、怎麼樣……」
「小子你找抽!現在可是我們頭兒在問你話!」姚三喝道,問案時如果有人想要刺探他們掌握的案情,照例都會讓手下人裝作發脾氣打斷發問。
薛捕頭又一抬手制止姚三,心平氣和地說:「狗子,你只要沒做虧心事,就沒什麼好怕的。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李大人府上丟了東西,現在正在盤查……這案子可不尋常,鎖頭沒壞裡頭的東西就沒了,簡直就像是狐狸借物一樣……」
「大爺,您說笑了,」狗子傻笑著說:「不打開箱子怎麼知道裡頭是什麼?就算能隔空取物,也不能不知道裡頭是啥就拿了去吧?如果有狐狸的話狐狸才不會幹這種傻事呢!所以說什麼狐狸借物,這都是沒影的事……一定是一開始就是個空箱子!」
「王八蛋!越說越得意啦?」姚三又一個大巴掌拍在狗子頭上罵道:「問你了嗎?你這沒皮沒臉的東西!」
狗子委屈地低下頭摸著腦袋不敢回嘴,薛捕頭直直瞪著狗子說:「你若是知道什麼,現在就說出來,不然可不要怪我沒給你機會……」他的雙眼灼灼,能把人看穿似的。
「大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怎麼敢動李大人府上的東西!再借我三個膽子也不成啊!我——」
狗子慌慌張張地一個勁搖頭,薛捕頭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說:「若真的不干你的事,你現在就可以滾了!府裡不平靜,瑞雲不會出來了,你就回去老實待著吧!叫你家少爺也安分點,別來添亂了!」
薛捕頭說完揮揮手讓他走,狗子的眼光轉向桌上那封被拆開的信,還想要拿,姚三就凶惡地瞪起眼來說:「還不滾?捨不得我們還怎麼的?想跟我們回班房喝茶嗎?」
狗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頭兒,你怎麼看?」老焦見薛捕頭若有所思的樣子,問了一句,想知道是不是要盯住那小子。
薛捕頭看著狗子垂頭喪氣的背影,想著這傻小子剛剛說了一句話:「不打開箱子怎麼知道裡頭是什麼?」
箱子的封條是李大人親手揭的,打開時所有人都看見箱子已經空了。
為什麼下書預告要盜天奪?
箱子嚴絲合縫,沒有機關也沒有從底部或側面被破壞的痕跡,只有箱蓋和箱子之間落了鎖之後有一僅能容髮的隙縫,天奪劍刃再薄也不可能從縫隙中取出。
薛捕頭把上了夾板的右手擱在桌上,左手指尖輕輕敲著桌面,看似漫不經心地看著茶棚外人來人往的大街,狗子的身影在人群中時隱時現,他就快要走到街口了。
突然之間,薛捕頭眨眨眼,一個壞笑從他的嘴角慢慢浮現,那是年少時鎮日在街上遊蕩,一肚子壞水的薛青原的笑容。
哼。薛捕頭在心裡冷笑了一聲想:這狗賊腦子倒好使。
李蒔言雖然是個王八羔子,可他有句話說得不錯:眼見非真。
「老焦,」薛捕頭左手食指一勾,老焦趕緊答應一聲附耳過去。「你去把肥牛給我叫來,有件事要給他辦……」
狗子出了茶棚頭也不敢回,走到街口才借著拐彎看了那夥官差一眼。
正好看見薛捕頭附耳囑咐兩個差人裡年紀大的那個,那位官差老爺聽了立刻出了茶棚,不知上哪去了。
一瞬間狗子還以為那差人是捉他來了,心頭一緊,差點竄上房頂逃了,可那差人出茶棚往城門的方向去了,並沒有朝他過來。
怎麼回事?難不成真給那捕頭看出什麼來了?狗子若無其事地轉過街角,心裡卻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如果真給他看穿了,現在就是逃走的最後機會……可如果他沒看穿呢?那輕舉妄動不就是不打自招嗎?驚動了官府能不能出城就難說了……
狗子咬咬牙,心想我可不能就這麼等著他來捉。這城中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藏身,只是那可不太舒服,皮肉之痛是免不了,這時候也說不得了。
一個老丐在街邊敲著破碗,狗子悄悄靠了過去。
「老大爺,跟您商量件事……」狗子一邊說一邊伸出手來,手裡抓著一把銅板,他慢慢放鬆手指,銅板叮叮咚咚地落進老乞丐那隻邊上有個缺口的破碗裡。
「欸?您、您這是……您要幹什麼就說吧!」老乞丐一見銅錢兩眼就直了,看看碗裡的錢,又疑神疑鬼地瞅著狗子,生怕他又把碗裡的錢一把抓回去。
「老大爺,您身上這身衣服就給我吧?」
「這、大爺您……說笑吧?」
「沒說笑。」
「您這叫我、我……難不成光著我這老屁股逛大街……」
「哪能呢?我是說咱換換……」
「您說真的?」老乞丐上下打量狗子一身粗布衣,雖然不是錦衣繡襖,可跟他這一身破衣爛褲比也是十分體面了。「小子,你……」老乞丐硬是沒說出下半截話:「是癡人還是傻子?」他現在一心只想趕緊跟這小子把衣裳換了,拿錢走人,等到這小子家裡人追來這事恐怕就要黃了。
騙這癡傻少年的錢他有些過意不去,可誰讓他家裡人由著他跑出來呢?這便宜不是我佔也會有別人佔,就當是老天接濟我一場吧!老乞丐想著心安理得地把破碗裡的銅錢倒進一隻小布袋裡,跟著狗子走了。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