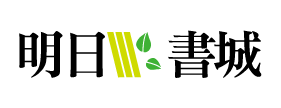會員登入
我要找書

-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推薦
- 目錄
- 內容試閱
特色
第八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作品
在我來的地方,有一個神祕的預言告訴我,你們和我都是七大寇的其中一員。而我們將要與六帝神對決,同時改造北境新的未來。
武俠小說老了,幸好我們還有──
沈默的結構武俠派
陳雨航:「《七大寇紀事》呼應歷史與現實,可說是一部武俠形式的世界革命史。」
同仇敵愾推薦
駱以軍、林俊穎、葉佳怡、神小風
白花是刑責之國,金烏是祭祀之國,朱輝是財富之國,藍關是飲食之國,碧海是聲色之國,黑水則是權勢之國。
而北境人在氣候和政教的雙重酷烈下,色情、生孕似乎成了唯一能夠放縱的事……
內容簡介
天衣憐魔是神風帝聯的頭號通緝犯。
他只有一個人,卻攪得神風帝聯威信全失,由東到西的六大主國:
白花、金烏、朱輝、藍關、碧海、黑水,沒有例外,他屢屢力挫之,
使六帝神頭痛不已。
有時他會想北境大地怎麼連一個思索的人都沒有,有誰敢和他一起公開抵制、
打擊神風教和神風帝聯呢?在這塊以信仰與政治粉飾過的暴力統治的土地上,
還有這樣的人嗎?但他想,總有一天,時代的風氣是會變的,即使這個過程很緩慢。
此時,他看到一個人影冒著風雪暴,正往北而去。那人要去哪裡呢?
天衣憐魔的心思振奮,他決定跟在那人的後頭,看看他到底要做什麼……
他透過預言,找到了另外六位同伴:夏緣霜,王隱,傲時問,石寒澈,
沈夢初和原雲蒼。七大寇從此之後,成為那個時代最不可思議的神奇人物……
沈默
武俠寫字人,1976年生,十月的男人,混過靜宜大學中文系、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試著演練書寫的技藝,試著留下黃金的事物,試著說出神聖的話語,試著在通俗與類型的範疇底,穿過邊界,以滲透更多變動與可能性,試著到字的內部,想像,夢遊,被巨大的火焰與深刻的雨水穿越,然後抵達、深入,到無人之境。已出版〈〈孤獨人三部曲〉〉、〈〈天涯三部曲〉〉、〈〈魔幻江湖絕異誌〉〉等多部小說,並以《誰是虛空(王)》、〈尋蛇〉雙料獲第五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評審獎及短篇小說獎參獎。主持【飛一般沉默~夢之零界域~】個人新聞台blog: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hensilent/
武俠寫字人,1976年生,十月的男人,混過靜宜大學中文系、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試著演練書寫的技藝,試著留下黃金的事物,試著說出神聖的話語,試著在通俗與類型的範疇底,穿過邊界,以滲透更多變動與可能性,試著到字的內部,想像,夢遊,被巨大的火焰與深刻的雨水穿越,然後抵達、深入,到無人之境。已出版〈〈孤獨人三部曲〉〉、〈〈天涯三部曲〉〉、〈〈魔幻江湖絕異誌〉〉等多部小說,並以《誰是虛空(王)》、〈尋蛇〉雙料獲第五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評審獎及短篇小說獎參獎。主持【飛一般沉默~夢之零界域~】個人新聞台blog: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shensilent/
自述
謝辭
引言
第一部:緩慢
第二部:相遇
第三部:無知(或者玩笑)
第四部:不朽
第五部:簾幕
第六部:身份(或者被背叛的遺囑)
第七部:不朽
後記:武俠革命以後,武俠自由以前,在武俠末華麗裡
謝辭
引言
第一部:緩慢
第二部:相遇
第三部:無知(或者玩笑)
第四部:不朽
第五部:簾幕
第六部:身份(或者被背叛的遺囑)
第七部:不朽
後記:武俠革命以後,武俠自由以前,在武俠末華麗裡
推薦
陳雨航(出版人、小說家)
沈默於傳統武俠小說的書寫,其顛覆與創新不從今日始。人性對社會正義的需求,俠骨柔腸的嚮往,依舊存在,但已不為己足。《七大寇紀事》依然有著武俠小說特有的浪漫基因,但已非純然的江湖恩怨、兒女情長可言,那種浪漫已被更高更廣的理想與視野涵蓋了。
斯巴達寇斯奴隸起義,黑澤明《七武士》武士結合農民抗暴……斑斑革命史蹟,以及反映現實的藝術,莫不使人們熱血沸騰。《七大寇紀事》呼應歷史與現實,可說是一部武俠形式的「世界革命史」。亟待摧毀的舊世界,其意識形態和制度與若干現實世情若合符節,呈現了強烈的現代感。作者思索並安排各種制度和措施建立虛擬實真的世界,觀念既現代又前進。新的觀念結合新的形式,作者不避當代新辭,甚至學術名詞、論述。章節結構嚴整,文字密度高。是部超越類型、現實感極強的現代武俠文學。
武俠江湖固有退隱的傳統,但那畢竟是身在山林,本就是一種避世的態勢,不同於此,《七大寇紀事》是一個革命成功的廟堂,打下江山而能自動引退者幾希,小說主角幾乎從神格降至平民化的身份以及功成之後的飄然遠去,動作一樣,卻具有更深遠的意義,令人心嚮往之。
葉佳怡(小說家)
在由六帝神統御的廣遼土地上,代表死亡的「喪君」是最先消失的創世之神,卻也是永恆存在的魅影。於是世間起落皆為雙面刃:「自由」的敵人來自外在壓迫,卻也來自身體衰敗;「武功」同時抗拒並接受世界,卻也是存活必然的自毀。沈默告訴我們如何以肉身抵擋存在的虛無,如何以排拒成全平等的自由,如何以傷慟啟程,再以完整的面貌迎向絕美末日。
作者後記
後記:武俠革命以後,武俠自由以前,在武俠末華麗裡
【大虛空記五部曲】終於來到第五部《七大寇紀事》,這是此一系列書寫計畫中的最後一部。從第一部的虛空王,到最後的七大寇,恰恰又回到溫瑞安的武俠角色,正成一個循環,也是我這三年間屢屢嘗試開發的書寫結構:環狀。
只是《七大寇紀事》不像《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有一明顯的雙向時間敘事,但仍然在各個方面都不難看到「環」的存有,如果閱讀中的你願意仔細想想的話。
說起來,波赫士〈環狀廢墟〉對我的影響十分重大。我意欲在小說徹底實踐他的想法,因此才有了《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而【大虛空記】最後的《七大寇紀事》某個程度來說也是我所能完成的、在廢墟上最淋漓的大幻影。
一開始,我對【大虛空記五部曲】的想法就是要每一部敘事結構皆不同,第一部《誰是虛空(王)》是多聲道獨白的噪音小說,第二部則是十三名人物的第二人稱敘事大集合,第三部《天敵》採用環狀書寫,以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正逆循環開展,第四部《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同樣是環狀書寫,但改為全第三人稱,以兩個人物際遇分開敘事,第五部《七大寇紀事》以說書人的引言帶出六十年的傳奇事蹟,將北境的當下與過往聯繫起來,是一種隱形(或潛行)的環狀結構之變體。很高興這樣子概念先行的書寫,我應該不算有搞砸,且不止是在武俠,就算是在嚴肅文學裡,也是初見或者少見的。
在溫瑞安寫下的眾多人物裡,最為吸引我的人物一直是沈虎禪。這個人的作為帶著某種特別的意味,尤其是他的思索與覺悟。而且他不介意自己為寇,擔當惡名這件事對他來說,顯然是無所謂的。他走他的正路上,即便變成他人口中的歪魔邪道,他亦是甘之如飴的(──這應該不難想到近來在漫畫英雄改編電影裡成為石破天驚之作的《黑暗騎士》吧)。
我不確定溫瑞安寫這個角色時是否一心讓他站在體制與權力的對面,但我在寫七大寇時則是紮紮實實地把這個層面演化開來。天衣憐魔一開始的人物原型確實是沈虎禪,當然後來天衣憐魔便脫離該角色的影響,自行其路,我投注了更多自己的殘片在天衣憐魔身上。實際上每一個七大寇都裝載著我的碎塊。這原來就是書寫的必然機制。你不可能禁止你所書寫的人物攜帶著你的某一些靈魂片段。
另外,七大寇的原型參考,自然不免要跟以下這些名作扯上關係,如《城邦暴力團》的七老、徐克的《七劍》、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乃至於黑澤明的《七武士》等等……
而其實,溫瑞安筆下的七大寇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確定的人選出來(一開始是五大寇,後來又變成六大寇,似乎溫瑞安初期還有點拿不準),主要是沈虎禪、溫柔、張炭、唐寶牛、方恨少五人,剩餘的兩個都還沒有真正現身。
但我的七大寇卻是一個都少不了,每個寇都有自己的故事想說、必須說。而七大寇要爭取的是就是自由。從武藝上的肉體自由,到擺脫神風帝聯階級統治的心靈自由。自由從來不是天生的,自由絕非只是一種愉悅姿勢而已。它很可能是與苦難孿生不棄不離的某種存有狀態。我的七大寇,如果說有什麼非說不可的意義,那必然是在於反叛,在於革命,在於思索吧。
這本書的武學系統特別要向詩人隱匿的第一本詩集《自由肉体》(雖然我更愛她的第二、第三本詩集《怎麼可能》、《冤獄》)致謝,七大寇江湖所用的武藝概念全都從自由肉體這四個字進行發想的。當然米蘭.昆德拉也是這本武俠最主要的精神支援者。小說每一部的名稱都是取自他的著作,並且竭盡我所能地描述與思索其書裡的各種觀點,將之轉換為武俠。而唐諾對個人戰爭的看法,以及本小說前頭所引用波赫士和卡爾維諾的文字,也都是我想要盡可能轉涉在小說行文之間的最好的觀點。我總是對這些偉大的書寫者充滿感激。因為有他們先行,我才能跟著後頭,逐漸走出一條崎嶇但自由的路徑來。
在多年以前,武俠曾經作為一充滿高度娛樂性的小說載體。但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是的,青春已逝去。自從2011年重新回到出版市場的《天敵》到2012年《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以及同年我開始擔任明日武俠電子報主編以來,至此我慢慢不得不接受武俠邁入老年時光的事實。電視、電影、電動、On-Line Game、智慧型手機,等等,無一不是武俠的天敵。武俠在這些大敵的環繞下,已經垂垂朽矣。盛世邈遠,武俠再也無法回復到強大的位置。這是不爭的事實。
武俠的壯年期已然宣告完結。從遠古時期的《刺客列傳》到古典時期(也是嬰兒期)的還珠樓主、平江不肖生等人,還有少年期的王度廬、鄭證因等人,乃至於金庸、古龍、司馬翎、梁羽生、溫瑞安、黃易諸雄所盤據的黃金現代(壯年時光),以及現在的,看來百廢待舉的武俠──我所處的當代,確確實實是武俠的老年期無疑了。
武俠的偉大時光已經完全燃燒殆盡了。我也不再存有興盛復還之的妄想。
但也因為武俠是老人了,無須再理會市場機制,再也不需要去迎合某些固定的標準,所以能大大方方、毫無顧忌地寫著心目中武俠最後的絕響。這是武俠可以全力開拓晚期風格的年代。
是了,武俠衰老,走進末世,但也因此獲得了接近純粹的自由。在當代的武俠,自由敘事、自由風格、自由概念的可能,屢屢獲得創新。於是,武俠便擁有了我的結構派(魔幻派)、黃健的解構派、徐皓峰的禪派、滄海未知生的未來派、施達樂的台客派、徐行的連環派、趙晨光的BL派、盛顏的耽美派、喬靖夫的狼派等等,這正是「武俠末華麗」之景,難能可貴,爾後恐怕再也不容易目睹如此新鮮活辣的、多種迷人風光崛起的時代吧。
當代最重要的知識份子艾德華.薩依德說的晚期風格(或者也會是日本大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的,晚年的工作),我想正可以拿來印證武俠的老年風景,既是不合時宜的,不圓融的,也是否定性的風格,更是不願意被收編的異類主體,薩依德寫道:「……你其實根本不可能在『晚』之後繼續發展,不可能超越『晚』,也不可能把自己從晚期裡提升出來,而是指能增加晚期的深度。……」他且說:「……它們超越它們的時代,在大膽與驚人的新意上走在它們時代前面,另方面,它們比它們的時代晚,也就是說,它們返回或回家,回到被無情前進的歷史遺忘或遺落的境界。……似乎完全座落他們時代之外,他們返回古代神話或古代形式,向史詩或古代宗教儀式尋求靈感。現代主義是弔詭的,它與其說是求新的運動,不如說是一個老化與結束的運動……」
我以現代語感重塑武俠句法、人物經歷、場景和武藝,甚至採用史詩格局及大量神話(魔幻)的氣氛加入武俠裡,或者其他武俠人屢屢借用他領域成分擴大、加深武俠類型的焦慮性作法,無不是對武俠晚期風格的具體表現──
我一方面感覺到我這一代武俠人的集體悲劇,但一方面又欣喜地品味終於自由的滋味。武俠就要毀滅了,然而正因為如此,它才能擺脫某些先天的要求與限制,走向更具有深邃感的境界。從某個面向來說,武俠也正在啟動革命。
而這是每一種衰亡的藝文類型都要面臨的局面。一如曾經大風光的歌仔戲或黃梅調,眼下也只能在國家戲劇院裡倖存。武俠或許和它們一般,都已經退出大眾的通俗場域,必須走向精緻與藝術(也就是少數化)的完成領域。
是了,我們這一批武俠人恐怕是武俠現代主義的第一線戰力,也是最後唯一的了。我們正在返回或回家,我們正在被歷史遺棄、遺忘。但我們也正在繼續增加武俠的深度,繼續走向一個古老與結束的,晚期的運動風格裡。
寫完【大虛空記五部曲】,我終於更明白武俠對我的終極意義。一意孤行地跟著武俠展開大膽而新意但其實又是衰弱而年老的冒險的我,在往後要寫的【武林異色譜】九大卷,必然會更覺得安心與自在。【大虛空記】有龐大的天下五區,我具體構造中州、東土、南域、西疆、北境的風土民情、武林生態,但到了【武林異色譜】,將要打散統一的概念,轉向更輕靈、更片段的武俠存在。
在這裡,真的要特別感謝編輯鄭建宗、主編劉叔慧的辛苦與支持,以及所有協助過這本小說成形的明日人,還有願意讀武俠的妳/你。謝謝你們願意和我一起繼續在武俠的蒼老餘生裡走這麼一段路。對我來說,是彌足珍貴的陪伴與見證。
接下來,我將會持續地書寫並目送著武俠緩慢而自由地走向墓穴,直到武俠消滅的徹底到來。而在武俠最後的歲月裡,也請你們跟我一起在解放後的武俠裡感受、呼吸它的全然自在吧。
精彩試閱
獻給媧,
始終小說是小說
我們是我們,
其中,不必然有牽扯與關連,
但所有思念都毫無疑問的
來自傾聽你
以及對妳傾訴,
而另一個事實是
始終
我都在傾全力地
為妳寫字。
自述
在時間的表面,小說以鐘的形式展示;
在時間的深處,小說以刺以一把劍的姿勢無可迴避地貫穿了書寫者如我。
謝辭
感謝米蘭.昆德拉,感謝波赫士,感謝伊塔羅.卡爾維諾,感謝法蘭茲.卡夫卡,感謝賈西亞.馬奎斯,感謝喬賽.薩拉馬戈,感謝張大春,感謝唐諾,感謝駱以軍,感謝董啟章,感謝娥蘇拉.勒瑰恩,感謝隱匿,感謝納博科夫,感謝黃碧雲,感謝朱天心,感謝朱天文,感謝舞鶴,感謝夏宇,感謝零雨,感謝艾蜜莉.狄金生,感謝鴻鴻,感謝辛波絲卡,感謝溫瑞安,感謝古龍,感謝金庸,感謝黑澤明,感謝徐克,感謝李安,感謝王家衛,感謝李啟源,感謝林書宇,感謝蔡明亮,感謝陳可辛,感謝羅貫中,感謝施耐庵,感謝保羅.策蘭,感謝,感謝蘇珊.桑塔格,感謝托爾斯泰,感謝福樓拜,感謝哈金,感謝顧城,感謝北島……
──更要感謝為了苦難與自由奮戰過的人們!
在哪一個地域都好,他們的鮮血與理想成就了我們現在太過習慣的自由狀態。後來的人濫用了自由,以致於我們正在付出代價,以致於自由的精神已遠遠被拋在自由的形式以後。也許是時候該重新檢視、理解自由的真義了。
引言
「怎麼樣的戰爭呢?也許有人計畫著更全面更積極更壯闊呼群保義的戰鬥形式,我個人的想法比較接近舊俄時代一個人挑戰彼時沙皇黯黑恐怖統治的亞歷山大.赫爾岑,以撒.柏林口中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他採取一種綿密不懈的、輕靈的游擊戰,一種他稱之為『我的哥薩克人小小戰爭』的自由不羈形式,呼嘯而來呼嘯而去,隨時隨地,無休無止,周旋到底。」
──唐諾《世間的名字》
「戰爭即將終結的時刻啟示著一個真理,一個平庸卻又根本,永恆卻又被遺忘的真理:面對活人,死者在數量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不是只算戰爭結束後的死者,而是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死者,過去的死者,未來的死者;它們確知自己的優勢,它們嘲笑我們,嘲笑生活的這個時間小島,嘲笑新歐洲這塊渺小的時間,它們讓我們明白這一切的微不足道,轉瞬即逝……」
──米蘭.昆德拉《相遇》
「……死亡隱藏在時鐘背後;死亡也隱藏在個別生命的悲哀中;在這片斷的、分裂的、不連貫的、缺乏整體感的事物背後;死亡,也就是時間,是個別的,分離的時間,朝向其終點不斷滾動的抽象時間。……如果直線是命定的、無可避免的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偏離』則能將此距離延長;假若這些偏離變得複雜、糾結、迂迴,或轉變得快速,以致於隱藏了本身的軌跡,誰知道呢──也許死神就找不到我們,也許時間會迷路,或許我們就可以繼續藏匿在我們那不斷變換的隱藏所在。」
──伊塔羅.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如果把一切存在都給予我們的話……存在將多於宇宙,多於世界。如果存在只給予我們一次的話,我們就將被消滅,將被取消,將會死亡。而時間則是永恒的饋贈。永恒允許我們連續不斷地得到這些經驗。我們有白天和黑夜,我們有鐘點,我們有分秒,我們有記憶,我們有當前的感覺,我們還有未來,這一未來我們雖還不知其形態,但我們能預感到或擁有它。」
──波赫士《波赫士全集Ⅳ》
第一部:緩慢
七大寇,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不可思議的神奇人物。請你們仔細聽著,我並不是在胡亂地吹捧,在往後的故事裡,你們將會與我一起明白、體驗這個事實。他們的存在,賦予這片天空、這塊土地的我們,截然不同的生活面貌與意義。
他們以人的姿勢告訴我們,憑藉著思索與行動,人不需要依靠神祇,也能創造自己的未來。你們要明白,北境的人、神共存姿勢,並非突如其來獲得的,而是浴血奮戰、從來不肯放棄信念的七大寇為我們爭取到的。
他們為我們示範了人的可能與高貴。他們告訴我們:你們不是神祇的奴隸,你們擁有自己的命運,你們需要開創與承受自己選擇的道路。他們說:你們作為人,決計不是生來就是為了被他人支使、奴役。
而這些你們已經習以為常的觀念,孩子們,請務必要專注地聽著,都不是沒有理由、猝然擁有的,那是經歷過一大段遲緩而艱困的日子才能棲居你們的腦海,實踐於生活之中。
故事啊每說一次,就是一次全新的驗證與檢視。
在這裡,我邀請你們跟我一起凝視與聆聽七大寇的事蹟,請你們聽聽看他們是不是真如我說的那樣不可抹滅,想想看他們是不是真如我說的那樣崇高不可動搖,是不是有了他們,北境才能有今日人只為人而戰的局面,是不是有了他們,北境才不至於在神風帝聯愈發殘暴、狂亂的統治下苟延殘喘而終於全數毀滅,是不是如我所言的,如果沒有他們,北境哪裡還有什麼可能,請你們聽,也請你們認真的想一想!
孩子,一個故事的被述說,就是想要回到記憶了找到安身之所。
我始終無法忘懷七大寇的行影。我的回憶提供他們持續存在的場域。我願意以他們在世間紀念者如此的身份而活。他們為北境人付出了多少,卻那樣快地被人扔擲到記憶的邊緣,好像從來不存在似的。這真讓人痛心疾首啊,不是嗎?在我們得到解放、得到自由以後,就應該輕易忘記當年那些在北境大地熱血奔馳、與神風帝聯幾十萬大軍經年作戰的七大寇嗎?
我應該怎麼述說他們的故事呢?長久以來,我總是困擾著要怎麼向如你們般陌生的孩子們開口說那個遙遠的昨日發生的種種。那是太殘酷而暴力的地獄風景。那是你們不曾親眼見證過的舊北境。
六十年了,你們的父祖輩集體丟棄昨日,連帶的也把帶給他們還有如今你們正品嚐著的這一切的肇始者都忘記了。我不是不能理解他們的想法,畢竟那是非人的歲月。而且教你們的父祖十二萬分羞恥的是,他們居然可以那樣適應地活著,毫不懷疑,深信那就是人天經地義的處境,直到七大寇崛起並到來以前,他們從來沒有為自己爭取更值得的人生。
孩子,他們是刻意遺忘的,你們的父祖啊恐懼去回想與正視往日,他們害怕,害怕發現原來今日在過的生活亦是幻影一場。從一無所有到忽然什麼都有了,他們只想要一再、一再地告訴自己,那本來就是你們生活裡有的,不是任何人創造的,是天生如此的。彷彿這麼一來就任憑誰也沒辦法奪走。但他們忘了一件事,如果根源、本來的面目遺失,如果他們不細細密密地認真思索與對待,北境人的未來還是有可能被拋回舊的路上──
這是為什麼我不得不在此跟你們說七大寇故事的緣由。
好了,七大寇,當然就是七個人,七個名字。他們各自具備獨特質地,但又擁有某種一致性。接下來,你們會逐步地知曉他們是誰,他們又是如何將北境人從神風帝聯以神為名的恐懼統治下解救出來。
重要的是:他們不是神,是人,有缺陷、恐懼但仍舊決定面對自身陰影的人。
當然了,所有的改變都必須漫長地持續著,且經歷相當緩慢的過程。一開始,誰都不知道他們可以,就連他們恐怕也不能想像自己爾後會牽涉、糾結著如此巨大的境遇與命運,並且那樣深深、深深地改變北境。
孩子們,讓我來告訴你們──有關七大寇的故事,有關他們的本事。
傲時問(一)
有沒有那樣的一個地方,一個無憂懼無受難無有欺凌侮辱的樂園?有沒有?
看見那個人的時候,他的眼淚還沒有終止,他一直在哭著,滿臉都花了,他渴望那個人降臨有多久啊,他就等著那個人來解救這一切,來停下煉獄風景的發生,來告訴他,生命還有值得活的,除了下賤以外,他還能是別的什麼。他哭著。
眼淚爬過他的臉頰,如蛇般冰冷,並迅速地結冰。
於是,他醒過來。夢中那人的身影迅速如一束光,遠離。他沒有選擇地醒過來。回到現實。他依舊還在這裡。在冰牢。一間狹小得長不過七步、寬不過兩步的石室,以溫石堆成,沒有置放床鋪,只有一堆白羽毛般的同眠草還有身上以獸毛與同眠草編結而成的衣物勉強可以保暖。這裡有許多這樣的石室。每一間都鎖著一個犯人。而他得保持移動,他不能就這樣睡去,他要起來,他不能躺著,只要一鬆懈,他就會萬劫不復,他必須離開留有體溫的同眠草。
起來啊,起來,為了你的女人,還有一家子人,你必須起來,不能再這樣繼續,難道你不想對得起他們嗎,如果想,就起來,你就得活著啊,活著,想活著,你就必須起來,必須,你就必須離開,離開那睡眠,離開舒適的狀態。
傲時問在心裡激勵著自己,並以雙手撐住身子,歪歪斜斜地坐起,打著劇烈的、不能抑制的哆嗦。好冷。縱使是打小習慣寒冷的他,亦受不了而今野獸般張牙舞爪地將他撕裂的寒氣──
這裡的確是終極的冰寒之境!
他站起身來,肌膚上的顫慄是一種實體,不停刺穿,像是有著尖銳小齒的毛蚤似的。傲時問咬著牙,僵硬地運動著,臉上剛剛淚水結成的冰棍隨著他的甩動,人上上下下的彈跳,不許久便喀啦喀啦地離開臉部皮膚。一陣燙傷般的痛楚持續在他裸露的臉和手部作用著。過了一會兒,他從同眠草下找出一條短木棍,反覆、反覆地練著同一個動作,舉棍,朝前方直刺,收棍,迅速而直接的肉體線條。
傲時問的臉本來烏青,肌膚也僵硬、腫脹,這是待在冰牢地的必然現象。但在他以棍刺前了幾百回以後,汗水滲出,臉色變為紅潤,肌膚亦回復適切的柔軟,有彈性。肉身顯然經由激烈的武藝練習獲得重新活躍的可能。
室外,暴雪正肆虐。呼嘯不停。他得以不怕有人聽見揮棍的聲響。如今還只是秋季,到了冬季啊,氣候的嚴酷將可想而知。他是在春季的時候來的。當時踏足處是滿地泥濘,適逢融雪時節,舉步維艱,到處都是碎冰布置,不是在地上與將醒的河川相依隨,就是從山邊落下。他幾乎是拖著三分之一的命被驅趕至此。不但手腳銬鍊行動不便,還得背負看管他們的地類人的行囊,苦不堪言。能夠僥倖不死,他感覺簡直是奇蹟。
同行原有七、八十人,不是中途凍死,就是不慎跌落山澗雪溝,屍骨難尋,到此處居然只剩不到二十人,就連三十八名的地類人,也有兩、三人死去。他這會兒所在位於猛雪山脈山腳的冰牢地,居住環境的惡劣可見一斑。
在這裡,負責看管他們這些罪人的獄衛根本不需費力,全年有七成時間都是暴風雪的天候,就是最強大而難以違抗的自動屏障。獄衛們鎮日只需巡守、點點人數,其他時間便窩在他們的石屋,烤火、飲酒、取暖,甚或強逼女人犯尋歡作樂,根本不虞有人脫逃。來到此處後,如傲時問這等被劃在野類位階的人,只能任憑魚肉,毫無反抗之力,是苟活或慘死,壓根不會有人在乎。
若囚徒稍有沖犯獄衛意圖的言語與舉動,用不著經過懲罰的程序,他們會直接予以處決。方法也很簡單,只消把人犯的衣物剝除,扔到房外,不出半個時辰,必然了帳完蛋。牢間裡雖然冷,但傲時問很清楚外頭的氣溫更是可怖。在狂暴的風雪之下,衣著再完備、再強壯的漢子也走不出一百步。如此一來,又有誰敢得罪在此地權威比六帝神更巨大、兇惡的獄衛!
然而,傲時問在抵達冰牢地前,就已經鐵了心、誓死要逃離此處。
他知道難度非常高。他在北境六大主國最偏北的白花主國,而冰牢地更在白花主國北方極邊遠處、高聳異常的猛雪山脈南向處。山脈以北,是絕無人跡、荒涼不知邊界為何的終日大冰原。山脈以南,則是綿延千食(註)、無遮蔽物的十絕高地。距離冰牢地最近的聚落,往南行走再快也要兩天才有可能到達,更別說若遭遇境內高壓、恐怖行事、到處稽查人民的白花軍會有什麼下場。而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在這等天候下說要離開,委實是痴心妄想。
然傲時問滿腔的恨意驅動著,令他比冰更冷冽、更強猛。他清醒地思考這一切,當朱輝七的城堡長當眾判他發配北方的刑責,而他一家人的血案卻只是隨口說說擇日再查時,傲時問就勢必要走上一條痛苦而漫長的謀反之路。
傲時問今年十七歲。他知道這一生幾乎已經是毀了。在冰牢裡,他最多最多只能殘喘個三到五年,屆時就算他們忽然良心發現將他放出去,他也已經是廢人。這裡的冰寒哪連骨頭都能夠穿透,即使他學過一點 受術,足以禦寒,但那只是最基本的呼吸法,就連武技都稱不上。他如果待在這裡,這仇這恨將綿延得永無盡頭,至死亦無休。不管怎麼樣,他都得離開防備鬆散的冰牢地,回到他的出生地,回南方的朱輝七城堡。
在那裡,有一樁滿門的血案等著他去結束,等著他了卻生死冤仇。
至於要怎麼逃出生天,從進來開始,傲時問便已著手準備。首先是每日的糧食,他總留下三分之一,幾個月下來居然讓他攢了足夠近百天的份量,尤其北狼肉他更是一口都沒吃的留著,連帶以同眠草與小野獸的皮毛編結完成的保暖衣物、帽、鞋、帳棚以及切割的刀具和特製棍子等,夾藏在屋內一角,就在幾大塊溫石堆疊產生的縫隙;其次是他小心謹慎地記住此地地形與獄衛的活動習慣,他沒有寫下來,而是牢牢地刻在腦海;第三點是他勤奮地鍛鍊攻術──
這件事著實有點奇妙,住在他隔壁房的一個神情疲憊、不知是年紀已大而白鬍白鬚白髮,還是因冰牢地的長久折磨而致此的老漢,教了他一套據說頗為強悍的攻術。
北境武學分作兩大系統:攻與受。受,主要就是練氣,將天地的氣息與肉身的氣息融會、貫通並囤積於內部、緩慢地強化五臟六腑與身體機能的技藝;攻,自然就是直接以身體造成破壞的功夫,包含拳腳和兵器使法等等,其運使天地之氣,只用不存,意在瞬間強烈的刺激肉身,達到具備巨大暴力的能耐,求全面衝擊刺殺,絕無退路。
兩者的重要差別在於傷與不傷。 受術,不攻;攻術,不守。兩派絕不相容。
受術求的只是自保,一般來說都是地類人以下的階級習練的。而攻術呢則主要是神類人、天類人,還有一些深受天類人寵信的地類人可以修習,至於役類人、野類人根本嚴格禁止,若被發現私下傳授攻術,即是犯罪,輕則如傲時問般發配遠地,重則處立決,無有轉圜空間。不過,實際上民間仍有人流傳攻術,但行事極為隱匿,且非緊要關頭,決計不用,只作為一種秘密的延續、傳承罷了。
受術呢,在於接受;攻術,在於擊殺。兩種武技系統正足以說明神風帝聯的上、下位階劃分之嚴明與統御之法則,其階級共有五種:神類、天類、地類、役類、野類。神類只有六人,也就是六大主國的最高權力之人,即六帝神。天類人則是帝神以下,被賦予部分治理主國權責的貴族群。神類和天類合稱為上二類。地類人則是直接服務天類人、執行各種任務的軍武層級。役類人嘛,即一般平民百姓,供神類、天類使役之用,有權有財的地類人亦可對役類人頤指氣使。至於野類人,則根本不算人,只是野獸,任一階級人皆可欺辱、戕害的類別。地、役、野等被統稱下三類。而被規定只能學至多不過是健身強體之受術的役類、野類,根本沒有能耐反擊,只能被予取予求。
處在冰牢地的傲時問還沒有清晰無礙地辨識到這等情勢,但已朦朧意識到北境五類人的不平不公,再不用多久,等他遇見那個夢中的人以後,神風帝聯統治面貌就會完全明白地映射在觀照,屆時傲時問將化作一頭具備終結性的猛虎。
另外還有一點要提的是,攻受分別的情勢,在約莫一百年前有了變化,主要是受術系統出了一曠世難尋的奇材──那是個瘦弱細小的役類人,在北境歷史裡甚至連個名字都沒有,役類人皆口耳相傳地喚他小宗師。意思是如果六帝神是六大宗師的話,那麼這個役類人自然只能是小宗師了。這個役類人呢讓神風帝聯的威嚴遭到史無前例的挑戰。只因小宗師的受術居然能夠擋住當時掌握黑水主國、六帝神之一神風越孤的槍神攻術,不但毫髮無傷,且在激戰一整日後,讓氣力透支的第一帝神不得不歇戰。
小宗師的受術本質就勝不了黑水帝神,但他驚人耐力與悠長氣息所導致的絕對不敗,告訴了其他人一件事:受術也有完全壓制攻術的可能。後來呢,小宗師聰明地逃離北境,往南而去,不知所終。
這是由於他的存在大大妨礙了尚武論強之神風帝聯之王者的權威。
要成為六帝神,得經歷非常嚴峻的過程。六帝神的傳承都是經過非死即生的武術競技產生。每當有一帝神死去,便要從現有的天類人選拔、替代,方法即舉辦帝神之戰,在擂台上,通過天類人的浴血搏鬥選出,就是父子兄弟也絕不會留情。帝神只能有一名,對參賽天類人來說,是沒得退讓的。戰況之激烈可想而知。每一次的輪替都造成至少千百人的傷亡。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