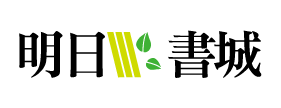-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
- 推薦
- 目錄
- 內容試閱
特色
繼《楊無敵》之後,慕容無言的全新武俠作品
「鐵瓦常鏽,琉璃易碎。
堅強的註定被消磨,華貴的必定遭遇多舛。」
江湖事,不過是一個爭字起頭,爭之後是奪,奪之後是恩仇,恩仇之後就是生死。江湖人,只要爭奪心一起,便是必定要走進生死門裡的。
學武之人是這個時代的眼中沙,看著人情世故看久了,也只能隨著眼淚流出來。
林俊穎、朱宥勳 專序
蔡國榮、譚光磊 推薦
內容簡介
必須先是個人,而後才是個江湖人──
淮軍還鄉的馬寶華與高楞子回到天津,打算謀求生計、過安穩的日子,但天不遂人願,忍辱求活卻遭遇種種欺淩與不納。後來因緣入了西泰魚行,還成為馬大把頭,一切都是因為袁大人發下的這十三個扳指之故……
以馬寶華為首的十二位當家人,也只是大家公推的首領,對他們有些微辭或陽奉陰違的也頗有人在。馬寶華知道自己絕不能倒下,他身後還有很多人在,夏六爺、高楞子、馬慧珠……這些人的活路,還有自己的活路,都需要繼續拚殺下去。
人這一輩子,就是「求活」這兩個字,向自己求、向旁人求、向世道求、向神佛求,可到頭來真能依靠的,還得是自己。
一輩子其實挺短的,忍一忍也就過去了。
推薦序 1
「現代」英雄的輓歌 ◎ 林俊頴
「俠以武犯禁」(『韓非子』),犯,以現代的眼光看,衝撞。因此,武俠與「現代」的衝撞,或必然是此類書寫創作者的一大挑戰。是面對、逼視以求變法維新,還是背向、遁逃繼續重複安全模式?是創作者的選擇,也是讀者的選擇。但既然是創作,書寫者是無所逃的。
今年的入圍決審作品,有勇氣拒絕遁逃而力圖突圍、創新、求變的可敬作者群,明顯闢出一條路徑,即是尋求跨類型的混搭與嫁接,他們攀援了奇幻、羅曼史,偷渡了吸血鬼、文學與電影頗富盛名的人物與場景,雜種之,狂歡之,但是否因此生出了武俠的新基因,有待看倌與時間大神裁決。
在這一場類型雜交嘉年華中,『鐵瓦琉璃』獨沽一味向歷史(劇)乞靈。嚴苛審視,我們得說他揀擇的並不是一條多新的路徑,然而他以強旺的企圖心縱身於神州大陸內亂外侮陵替、哀鴻遍野的現代歷史,全書始於清光緒廿六年、庚子、一九OO,結束於一九五二年,分為五部,外加七少爺的外傳做為閱讀紅利,細膩地羅織一群人的恩怨情仇,將半世紀的殘酷劇場聲色俱厲架在我們眼前。我個人感佩作者的耿耿一念,抗拒「歷史是勝利者所寫的」主流意見,遙向司馬遷太史公致敬,「遊俠列傳」不就是這樣言為心聲:「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確實,匹夫之俠,正是從「甘肅省環山堡淮軍老營」退了軍籍慘淡回鄉的馬寶華(保衛中華?)、高楞子,也是天津「鍋伙」的夏六爺、悶三爺、黃五爺(華夏炎黃子孫悶啊?)諸人,與其說作者塑造人物,更覺得他意在牽引讀者下視這一群萬物芻狗、碗筷敲得噹噹響的販夫走卒,歷史對他們何其殘酷,何其諷刺,歷經跨世紀、改朝換代的連年戰亂,陳腐的封建體制雖然瓦解,誕生了民主、科學為大纛的新中國,即使是用心如日月的匹夫之俠,又能如何?還不是亂世螻蟻,求苟全性命亦不可得。
全書五部,作者別出心裁以萃卦、豫卦、損卦、節卦、遁卦五個卦象開宗明義,往返剝復,這用以統攝全文脈絡的古文明遺產,豈不也是統攝了武俠的正統與道統的源頭之一?然而鐵錚錚的事實、歷史的進程,當文明古國遇上了現代化的西方列強,概括承受所有苦難的是誰?相對於這一群「苦俠」(評審蔡國榮先生精確的形容),聰明迷人、喝過洋墨水「師夷長技」的鑲黃旗貴族七少爺,是作者處心積慮營造的另一悲劇人物,雙方匯流,高潮處不是他點撥未受啟蒙的鍋伙現代商業的利潤、壟斷觀念,也不只是馬寶華以一口酒劍壞了七少爺謀炸孫中山的大計,作者或更要大聲質疑的是,當武俠撞擊「現代」,會是如何的局勢?理性、除魅的「現代」譬如書中一個比一個更高強的敵人,可還有武俠揮灑的生存空間?作者如此不迴避「現代」,是否置武俠小說於「演化的右牆」之絕境?
有此一說,「武俠是成人的童話。」此話貶大於褒吧。我個人有限的閱讀經驗,卻看到『鐵瓦琉璃』這樣的作品陸續出來,告別祕笈、洞窟、超能力、唐宋元明的漫天迷霧,無異自廢(舊)武功,卻是開創另一個壯闊、深沈的江湖人世。雖然選擇這樣的撞擊,創作更是艱辛,但魯迅的骨氣名言:「地上原來是沒有路的,只是因為走的人多了,便走出了路來。」
推薦序 2
掙與躲,安穩日子的(不)可能:序《鐵瓦琉璃》◎ 朱宥勳
《鐵瓦琉璃》全長二十五萬字──這是我在word裡按「字數統計」才知道的,實際讀起來非常暢快,並不覺得有這麼長──以一種極為寫實的筆法,描述了清末民初發生在天津市井的一段故事。用「寫實」來描述武俠小說,感覺有點奇怪,因為「武俠」此一文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允許奇幻場景的,但這確實是我讀完之後的感覺。這或者是因為它的主題非常古典,基本上與二十世紀左派、寫實主義的小說是類似的,它始終探問:在那樣的社會裡,一個普通人如何能夠過上安穩的日子?
這問題,似乎早在小說開始沒多久,就由七少爺說出了答案:「安穩日子是自己掙出來的,可不是躲出來的。」縱觀整部小說,馬寶華正是踩在這條由「躲」到「掙」的軸線上,起初為了安穩日子離開軍伍、忍氣吞聲,後來卻要重返軍中、擔當把頭才能過上一點正常生活。然而,有趣的是,從小說的情節發展看來,與其說七少爺這句話說出了小說主題,不如說這是作家藉七少爺之口提出的「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整篇小說正是不斷在挑戰、否證這個「掙」字:躲是躲不出好日子的,但掙就掙得到嗎?
這個提問放在武俠小說的脈絡下來思考,非常值得玩味。武俠小說本質上是描寫「有著超乎常人的武力的主角」的故事,它可以視為華人版本的超級英雄敘事(類似於美國的「蜘蛛人」)。在這樣的故事裡,由於主角能力超乎常人,所以就有著超乎常人的倫理責任,小說的重心就是「他(們)拿這樣的能力去做什麼?」整趟小說,往往就是驗證此一倫理責任的旅程,此即武俠的「俠」字所在,它帶有道德價值上的指向性,這也是為什麼傳統的武俠很容易開展出正邪對立的框架的原因,也常常連結到一種巨大的良善意圖當中。我們可以直接從金庸的經典名句看出這種傾向,他環繞著郭靖建構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形象。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鐵瓦琉璃》的主角,馬寶華(與高愣子等人)所接受到的倫理任務就很有趣了,它僅僅是一個縮得很小的願望──他們想利用那點能力過上安穩的日子,再有的話,就是希望身旁的人也過上安穩的日子。
必須要有這麼不平凡的能力,才能試著去「掙」這麼平凡的目標,這種反差本身就饒富興味。為什麼這個目標這麼難?自然是因為角色們活在最不可能安穩的中國近代史當中。從民變、義和拳、八國聯軍、革命、帝制復辟到中日戰爭的前夕,每一個時點都是可能擊碎生活的大挑戰,馬寶華的艱困不在於他沒有本事,而在於這個世界鉅變的當下,一身的本事並不能保證他得到自己想要的。這樣看來,其實這篇小說也連結著晚近中國小說「感時憂國」的主題。他們一次次地化險為夷,除了情節上的曲折之外,也讓我們看到那個時代的中國地方勢力如何化解每一波外力衝擊,社會團體之間如何互動求生。終歸一句話,「你以為好日子就能來得這麼容易麼?」
我特別喜歡其中兩個設計,其一是馬寶華的妻子杜翠芹,在篇首巧妙埋下的伏筆(馬寶華初回家見妻子那整段對話寫得真好!),牽動引爆了後半段的所有困阨,扣緊了「安穩的生活」裡面的陷阱,與其難以達成──不只是外力讓你無法護持一個小家庭的生活,連家庭本身都會成為問題。另一個點則出現在外傳〈摘星掩月〉裡。在這個中篇當中,本傳裡才智過人、卻象徵著舊時代最後守護者的七少爺被寫得極為立體,也交代了為何無論外國勢力如何欺凌他都能隨順時勢,卻拚著一死也要刺殺孫中山的曲折心思:
「爺我天生就是爺,打在娘胎裡的時候就是爺!爺沒想過要欺負你們、禍害你們。可爺時運不好,被革命了、被造反了,被袁世凱夥同著孫大炮把天下騙走了,爺以為就換了世道,可誰知道換湯不換藥!天底下就沒有過太平世道!爺如今忍氣吞聲地做了孫子,不想招誰、不想惹誰,爺就想每天三飽兩倒一個澡的過日子,這都不行?這都礙著你們了?非得把爺擠兌死你們就開心了?爺死也不讓你們開心!也死也不讓你們得意!爺我就不給了!」
「就不給了」,代表本來是可能給的。代表他再三哀嘆的「欺我大清無人」,並不是他憤怒的主要原因。大清有沒有人,國家道統是否維繫,都還沒能逼得七少爺義無反顧,真正的癥結恐怕還是「安穩的生活」被毀了──每天三飽兩倒一個澡的過日子,這都不行?這一個側面,不但讓七少爺這個角色厚實起來,也讓整部小說的思維更清晰地浮現了,這是一個現代性入侵的腳本──而且是遠比二十世紀大多數有心經營此主題的「純文學」作品,更有血肉,更紮實的,充滿真正的民間細節的腳本。
而就在結局裡,我們看到了作家心目中,這趟「掙」之旅的極限,即日本勢力的入侵。小說結束在一個幾番幫助過馬寶華的日本人,要求馬寶華交出漁行碼頭以便日本轉賣軍火。不像前面幾次挑戰,馬寶華這次似乎終於用盡了機緣、能力、人脈,只能像當年黃五哥一樣,燒了漁行以消極抵抗,最後不知所終。這迅速急轉直下的結局意味著什麼?為什麼作家選擇在這裡讓馬寶華徹底失敗?除了人已老去這一情節自然發展之外,還有沒有更進一步的意義?我覺得關鍵或許就在「有恩」這個點上。日本作為一個與中國交纏前進,同時摸索著現代性之路的國家,其實並不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是完全的他者。「日本鬼子」終究比「洋鬼子」親近一層,但也正因為這種熟悉,使得抵抗變得更加複雜了。而就從這裡此開始,中國近代社會將轉型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模式,進入我們這位舊時代的「俠」所完全不能面對的世界。那種馬寶華等人追求一生的,舊的「安穩的日子」──那是以為帝制復辟之後,好日子就會重回的天津小民的想望──終於再也不可能了。
作者後記
這本書你能翻至此頁,很是可以坐下來,在紙上奉茶閒聊了。
現在的時光中,有閒暇看書的人真不多,因為其它可見的東西太過精彩,連3D都不足過癮,還要IMAX才酣暢。但從百餘年之前,上溯至倉頡造字的幾千年裡,卻都是用枯燥的文字紀錄歷史。讓今人捧讀起來,在字裡行間暢想當初的滄桑。
但歷史也不盡是都躺在那些精裝的書匣子中,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或在於隻言片語,或在於口口相傳,數行文字裡就藏著一段舊時代的精彩。
比如這本書裡就寫有會功夫的人如何翻牆越脊,其實這與招式、拳架、方藥一樣,都是代表著門派的師承關係,有明顯獨特風格的標籤。江湖人一看痕跡,就能判斷出來者是那門那派,與自己是何種關係,自己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對待。而千里之外同門初見時,口說無憑,將師傅教過的東西露一點出來,也有亮明身份的意思在內。
有的江湖人獨自到陌生地方打尖吃飯,手邊必要擺一碗醋,不是用來拌菜下飯,而是驟遇危機時含在嘴裡噴人,為在交手時占得先機。這就是走江湖的老師傅們,常在荒村野店中經過,用自己的經驗給後輩留下一個護身保命的法子。
再看當年老拳師們合影的舊照片,很多人要手握一把烏骨長柄紙扇,這不是老人家們要附庸風雅,而是這紙扇另有用處。人到老年,再隨身攜帶刀劍就不合身份,平日迎來送往的應酬增多,兵刃隨身也不禮貌,但習武產生的危機意識和防護習慣卻依然存在。這時候一把紙扇掉過頭來緊攥在手中,功效真能抵得上刀槍。
活在江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行俠仗義,那是評書裡大俠要幹的事,自己要做的第一事情是保命。保自己的命,也保別人的命。綠林的朋友在城外呆久了,想要進城來快活,是決計不會住客棧的,不是住不起,而是不應該住。他們進城必須要住在鏢局,外出都有鏢師陪同,一是為了保護,二也是為了管束,不讓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來,給官府添麻煩。而鏢局不能拒絕接待,更不能讓對方在自己的地界裡出事。一旦出了意外,也就鏢局壞了名聲,這杆鏢旗就走不出城門了。
這些,都是可供茶餘飯後做談資的小故事,無數此類小故事,如拼圖般,構成了另一個角度的江湖;一個不見大俠、盟主,只有販夫走卒的江湖;一個百年前曾經活生生存在過的江湖;一個曾與我們擦肩而過的江湖。
《鐵瓦琉璃》這部書名是憑空躍出筆尖的,四個字未曾有刪改或更替,就這麼渾然天成的出現。想來它最能代表這個曾存在過的江湖的格局,高貴與卑微、坦蕩與猥褻、快意與悲愴、壯烈與苟活。江湖人行江湖事,江湖事就在江湖人之間碰撞。
鐵瓦常鏽,琉璃易碎,堅強的註定被消磨,華貴的必定遭遇多舛。江湖終會在無聲無息間演進,又再瞬息中巨變。銀號通兌與匯款,瞬間淘汰了鏢局;槍械流入民間,瞬間淘汰了護院武師;而人性的日漸沉淪,更讓堅守道義的人無所適從。
於是,江湖很快就成了故事。人們在談論起江湖來,口氣與心態,就如講故事一般。就像遠遠指著一座漸漸風化所剩無幾的空城,講述它當年的繁華種種。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被打破了,才值得懷念,越珍貴,懷念的便越多。若是如今比當初更好,那又何必懷念?其實人們對江湖的懷念,並非在於當時的刀光劍影,或者俠骨柔腸,人們更多懷念的,而是當時的故事。
而這本書就是在講故事,想借書中人的舉手投足,穿起無數碎片,將那個曾經存在過的江湖幻化出來。給你看。
你若喜歡,我便欣慰。
試閱
故事從一九○○年八國聯軍進犯北京開始,至一九二○年凡二十年間。淮軍還鄉的馬寶華與高楞子回到天津,願過安穩的普通人日子謀求生計,但天不遂人願,忍辱求活卻遭遇種種欺淩與不納。二人被迫流入江湖,在搏殺與爭鬥中求生。在這個新舊交替紛雜巨變的新時代中,無數與他們相仿、如草根般卑微之人艱難求活。
第一部 兌上坤下
兌上坤下者,卦象澤滿大地,君子瘁心於職。
清光緒二十六年,甘肅省環山堡。
太陽剛剛從天邊露出一絲眉目,附近的夜空正在變成淺淡的灰色,從東邊開始向西慢慢鋪陳開來。另一邊,下弦月與星光還猶自在漸漸縮減的夜幕中堅持著,像是要掙扎著再多看這大地一眼。
山寨裡已經有屋子開始燃燒,橘紅色的火光透過屋簷與山石時隱時現,呼喝聲與慘呼聲卻比方才又遠了些、也弱了些,應該是攻山的袍澤們又殺進去了幾十步的樣子。勝負已定,整個山寨被蕩平只是時間問題。
馬寶華無心追上去與袍澤們分功,他拄著撓槍倚在洞開的寨門上,身上從內到外的感覺疲乏。撓槍是從湖北傳過來的兵器,在槍頭上加裝一個鐵鉤,在槍尾上加一個鐵環,除廝殺外還有攀爬的功用,善用的好手揹幾把在身上,翻牆爬山如履平地。方才就是馬寶華與高楞子又一次借助撓槍悄悄爬上寨牆,殺死哨兵打開寨門接引大隊軍馬進入,將躲藏在裡面的米勒教眾殺了一個措手不及。
潛伏、爬牆、摸哨、開門、殺賊、記功……這些事日復一日不斷地重演,令馬寶華覺得越來越累,像是被蒙了眼圍著磨盤只管向前走的驢。這種感覺令他開始害怕,半夜睡不著的時候,他覺得這是自己要死在這裡的前兆。
今天又一次打開寨門後,馬寶華仰望天空愣了好半天,終於從依靠著的門板上挺起身子,招呼高楞子道:「楞子,跟我回天津吧,咱不幹了!」
淮軍老營裡,老常蹲在大通鋪上慢慢抽菸,看著神情專注收拾行裝的馬寶華,嘆口氣問道:「真走啊?不改啦?」
馬寶華點點頭,手中不停,嘴裡應道:「真走,出來都四年了,真想老婆孩子。再說了,這兵當得什麼時候是個頭?年年欠餉,帶著欠條子替朝廷賣命到什麼時候?」
老常半晌無語,又是嘆口氣。馬寶華說的是大實話,大清的八旗兵早不行了,綠營到了咸豐年間也爛透了,不然怎會讓洪秀全從廣西一路殺到南京占了半壁江山,現在放眼天下,能打的也就湘淮二軍。人說「中興將相,十九湖湘」,定亂後,湘淮軍中位列總督者前後計十五人。可打贏了卻要被裁汰,裁汰著還不補足欠餉,將人逼得譁變了,又讓沒被裁的去打殺那些昔日袍澤,這兵還怎麼當?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該那麼賣命去跟長毛、撚子拚殺。就剩下的這幾營兵,先前駐在山西也是多遇刁難,要嘛沒嘛,非等到這裡出了白蓮、那裡起了彌勒,才想起這營能打的兵來,騾子一般地被撥來調去。這些當官的老爺們,是把打仗當成下棋麼?
老常伸手入懷,摸出個小包囊遞過去,馬寶華接了打開看,裡面是半吊銅錢、幾枚銀戒指、半個銀鐲子,還有一塊煙土。他明白這是同棚袍澤的籌措,點點頭道:「多謝兄弟們,將來有命到了天津,來煤廠胡同找我,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出生入死的情誼,背靠背保命的交情,不論放在什麼時候都忘不掉。
這時屋門一開,邁進來身材不高卻細腰寬肩膀的高楞子,甕聲開口道:「哥,劉糧台說了,騾馬是軍產,你要想用得拿營官手令去。」
馬寶華冷笑一聲,回頭衝老常道:「看見了吧,都說人走茶涼,這人還沒走呢,劉麻子這人性你就看出來了吧?你以後防著他點吧,別聽他『老鄉老鄉』那一套糊弄咱們。」他轉頭又道:「不給咱也能走,有隨軍的商戶能把咱一路帶回天津去,收拾你的。」
老常眼神一黯,卻手指這剛進門的高楞子問道:「你要把他也帶走?他可是把打仗的好手哩。」
馬寶華看了看盯著自己的高楞子,回頭道:「躺進地下的那些兄弟,哪個不是好手?你再好總會遇見比你更好的。這孩子全家都沒了,就剩這根香火,給他留條出路吧。他跟我回天津,我找個好鋪子送他進去做學徒,三五年的熬出來,娶媳婦生孩子過安穩日子,不比在這用命換欠條子強?」
老常點點頭:「跟你走也好,這孩子就聽你的話,別人也使不動。行啦,咱爺們有緣的話,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馬寶華揹了包袱走出營外,回頭望向無力垂在旗杆上的將旗,遠處是連綿的黃土坡,沉寂的堆磊在天際之下。
高楞子跳著跑來:「哥啊,都說天津衛裡遍地是黃金咧?」
馬寶華笑道:「遍地是黃金?那我還用得著跑這遠來麼?不過沒有遍地黃金,卻有太平日子等著咱,走咧!回家過太平日子去!」
高楞子雀躍著,一個跟頭從坡上躍下去,腳底下帶起來陣陣黃塵。
湘淮軍所謂隨軍的商戶,實際上就是收贓的販子。因為按照大清的軍制,八旗以及綠營是拿朝廷餉銀的,旱澇保收。湘淮軍則屬於「勇」,只忠於自己的上司,所以軍權更替都是在兄弟、父子間進行,其糧餉也由統軍者自行籌辦。歷來湘淮軍軍餉除去戶部撥款、厘金籌辦、勸捐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賊贓,說直白一點就是劫掠。所以曾國荃攻破南京城之後,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封城斂財,第二件做的事就是阻攔友軍進城,第三件做的事就是放火滅跡。
隨軍商戶的經營就是跟著老營,每到大戰之後便備好金銀銅錢,把兵勇們從「敵人」那裡搶奪來的物件挑揀收購,再運到別處販賣,同時也兼著替他們往家中匯錢、通信的事情。這生意利潤極大,風險當然也極大。這次鄒商戶帶著十幾車的牛羊皮子回天津,正好帶馬寶華與高楞子一路,這既節省了兩人的腳力,不用千里徒步風餐露宿地走回去,同時他也省了雇傭保鏢看護貨物的費用,可謂是雙方互利的好事。
人與人之間,最常見的就是這般關係,自己有用才會被別人用得著,才能在被別人利用你時侯,藉機達到自己的目的。你若是在別人眼中毫無用處,那除了至親之人外,怕少有人會樂意幫你。很多人也如同鄒商戶一般,把那些平日笑臉相迎的「朋友」們,在心裡分成兩類,一類是能用得著的,一類是用不著的。分類不同,對待時的態度自然更不相同。
一行人車過大同、靈丘、涿州、廊坊,直奔天津。
這一天早早出了客棧上官道趕路,按慣例是高楞子騎馬走在前面開眼,後面是鄒家商號的夥計,馬寶華坐在第三輛車的貨包上前後照應。沒走多遠就看見前面走過來主僕三人,中間是個騎馬的錦衣少年,大約十五六歲的樣子,大辮子油亮地盤在脖頸上,有僕從走在他馬前牽著韁繩,另一個僕從騎一頭青色毛驢跟在後面。
白天時,我是一個房地產行業的初級管理者,被郵件、報表、核算、統計等等諸多亂事裹挾。在夜晚,我是個沉浸在自己所構築故事中的旁觀者,看著筆下人物在字裡行間中躍動、奔走、歷盡悲喜。一個人,能有兩幕舞臺,互呈精彩,真是件頗為幸福的事情。
看《一代宗師》中有對習武的三重境界,見自己、見天地、見終生。寫手作文也是如此三重,先編故事給自己看,再用筆摹世間故事,最後在故事中包容天人萬物。我寫字八年,自覺還在第一重境界內尋窺門徑,所以從未敢稱「作家」,只敢說自己是個寫手。
而我的故事裡,絕少會出現大人物,帝王盟主、才子佳人;我更多是在記述著平凡人所作所為的不平凡事。因為我覺得,唯此才更可歌可泣,唯此文字,才能對那些以平凡之身成就奇跡者,用文字呈上一份尊敬。
這就是我,用平凡文字講述平凡人不平凡故事的說書人慕容無言。
第二部 雷上坤下
第三部 艮上兌下
第四部 坎上兌下
第五部 乾上艮下
外 傳 掩月摘星
後 記
第一部 兌上坤下
兌上坤下者,卦象澤滿大地,君子瘁心於職。
清光緒二十六年,甘肅省環山堡。
太陽剛剛從天邊露出一絲眉目,附近的夜空正在變成淺淡的灰色,從東邊開始向西慢慢鋪陳開來。另一邊,下弦月與星光還猶自在漸漸縮減的夜幕中堅持著,像是要掙扎著再多看這大地一眼。
山寨裡已經有屋子開始燃燒,橘紅色的火光透過屋簷與山石時隱時現,呼喝聲與慘呼聲卻比方才又遠了些、也弱了些,應該是攻山的袍澤們又殺進去了幾十步的樣子。勝負已定,整個山寨被蕩平只是時間問題。
馬寶華無心追上去與袍澤們分功,他拄著撓槍倚在洞開的寨門上,身上從內到外的感覺疲乏。撓槍是從湖北傳過來的兵器,在槍頭上加裝一個鐵鉤,在槍尾上加一個鐵環,除廝殺外還有攀爬的功用,善用的好手揹幾把在身上,翻牆爬山如履平地。方才就是馬寶華與高楞子又一次借助撓槍悄悄爬上寨牆,殺死哨兵打開寨門接引大隊軍馬進入,將躲藏在裡面的米勒教眾殺了一個措手不及。
潛伏、爬牆、摸哨、開門、殺賊、記功……這些事日復一日不斷地重演,令馬寶華覺得越來越累,像是被蒙了眼圍著磨盤只管向前走的驢。這種感覺令他開始害怕,半夜睡不著的時候,他覺得這是自己要死在這裡的前兆。
今天又一次打開寨門後,馬寶華仰望天空愣了好半天,終於從依靠著的門板上挺起身子,招呼高楞子道:「楞子,跟我回天津吧,咱不幹了!」
淮軍老營裡,老常蹲在大通鋪上慢慢抽菸,看著神情專注收拾行裝的馬寶華,嘆口氣問道:「真走啊?不改啦?」
馬寶華點點頭,手中不停,嘴裡應道:「真走,出來都四年了,真想老婆孩子。再說了,這兵當得什麼時候是個頭?年年欠餉,帶著欠條子替朝廷賣命到什麼時候?」
老常半晌無語,又是嘆口氣。馬寶華說的是大實話,大清的八旗兵早不行了,綠營到了咸豐年間也爛透了,不然怎會讓洪秀全從廣西一路殺到南京占了半壁江山,現在放眼天下,能打的也就湘淮二軍。人說「中興將相,十九湖湘」,定亂後,湘淮軍中位列總督者前後計十五人。可打贏了卻要被裁汰,裁汰著還不補足欠餉,將人逼得譁變了,又讓沒被裁的去打殺那些昔日袍澤,這兵還怎麼當?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該那麼賣命去跟長毛、撚子拚殺。就剩下的這幾營兵,先前駐在山西也是多遇刁難,要嘛沒嘛,非等到這裡出了白蓮、那裡起了彌勒,才想起這營能打的兵來,騾子一般地被撥來調去。這些當官的老爺們,是把打仗當成下棋麼?
老常伸手入懷,摸出個小包囊遞過去,馬寶華接了打開看,裡面是半吊銅錢、幾枚銀戒指、半個銀鐲子,還有一塊煙土。他明白這是同棚袍澤的籌措,點點頭道:「多謝兄弟們,將來有命到了天津,來煤廠胡同找我,有我吃的,就有你們吃的。」出生入死的情誼,背靠背保命的交情,不論放在什麼時候都忘不掉。
這時屋門一開,邁進來身材不高卻細腰寬肩膀的高楞子,甕聲開口道:「哥,劉糧台說了,騾馬是軍產,你要想用得拿營官手令去。」
馬寶華冷笑一聲,回頭衝老常道:「看見了吧,都說人走茶涼,這人還沒走呢,劉麻子這人性你就看出來了吧?你以後防著他點吧,別聽他『老鄉老鄉』那一套糊弄咱們。」他轉頭又道:「不給咱也能走,有隨軍的商戶能把咱一路帶回天津去,收拾你的。」
老常眼神一黯,卻手指這剛進門的高楞子問道:「你要把他也帶走?他可是把打仗的好手哩。」
馬寶華看了看盯著自己的高楞子,回頭道:「躺進地下的那些兄弟,哪個不是好手?你再好總會遇見比你更好的。這孩子全家都沒了,就剩這根香火,給他留條出路吧。他跟我回天津,我找個好鋪子送他進去做學徒,三五年的熬出來,娶媳婦生孩子過安穩日子,不比在這用命換欠條子強?」
老常點點頭:「跟你走也好,這孩子就聽你的話,別人也使不動。行啦,咱爺們有緣的話,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馬寶華揹了包袱走出營外,回頭望向無力垂在旗杆上的將旗,遠處是連綿的黃土坡,沉寂的堆磊在天際之下。
高楞子跳著跑來:「哥啊,都說天津衛裡遍地是黃金咧?」
馬寶華笑道:「遍地是黃金?那我還用得著跑這遠來麼?不過沒有遍地黃金,卻有太平日子等著咱,走咧!回家過太平日子去!」
高楞子雀躍著,一個跟頭從坡上躍下去,腳底下帶起來陣陣黃塵。
湘淮軍所謂隨軍的商戶,實際上就是收贓的販子。因為按照大清的軍制,八旗以及綠營是拿朝廷餉銀的,旱澇保收。湘淮軍則屬於「勇」,只忠於自己的上司,所以軍權更替都是在兄弟、父子間進行,其糧餉也由統軍者自行籌辦。歷來湘淮軍軍餉除去戶部撥款、厘金籌辦、勸捐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賊贓,說直白一點就是劫掠。所以曾國荃攻破南京城之後,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封城斂財,第二件做的事就是阻攔友軍進城,第三件做的事就是放火滅跡。
隨軍商戶的經營就是跟著老營,每到大戰之後便備好金銀銅錢,把兵勇們從「敵人」那裡搶奪來的物件挑揀收購,再運到別處販賣,同時也兼著替他們往家中匯錢、通信的事情。這生意利潤極大,風險當然也極大。這次鄒商戶帶著十幾車的牛羊皮子回天津,正好帶馬寶華與高楞子一路,這既節省了兩人的腳力,不用千里徒步風餐露宿地走回去,同時他也省了雇傭保鏢看護貨物的費用,可謂是雙方互利的好事。
人與人之間,最常見的就是這般關係,自己有用才會被別人用得著,才能在被別人利用你時侯,藉機達到自己的目的。你若是在別人眼中毫無用處,那除了至親之人外,怕少有人會樂意幫你。很多人也如同鄒商戶一般,把那些平日笑臉相迎的「朋友」們,在心裡分成兩類,一類是能用得著的,一類是用不著的。分類不同,對待時的態度自然更不相同。
一行人車過大同、靈丘、涿州、廊坊,直奔天津。
這一天早早出了客棧上官道趕路,按慣例是高楞子騎馬走在前面開眼,後面是鄒家商號的夥計,馬寶華坐在第三輛車的貨包上前後照應。沒走多遠就看見前面走過來主僕三人,中間是個騎馬的錦衣少年,大約十五六歲的樣子,大辮子油亮地盤在脖頸上,有僕從走在他馬前牽著韁繩,另一個僕從騎一頭青色毛驢跟在後面。
馬寶華坐在貨包上攏目遠望,心中暗想這是哪家的少爺,能起這麼早趕路,於是不由得就多望了幾眼。
眼見兩行人交錯而過,騎馬的少爺上下打量了高楞子,忽然冷哼一聲,抬手一馬鞭抽在高楞子身上。
這一鞭又響又脆,不但把高楞子打驚了,也把鄒商戶的整列隊伍都打得一停,諸人收住腳步紛紛矚目看向那錦衣公子。錦衣公子眉頭緊皺,馬前後的兩個僕人面色大變,也立住腳步。
那公子抬手又是一鞭抽到,直奔高楞子的面門。
高楞子在馬上仰身閃過,順勢翻落到馬內側,拉住韁繩用馬身護住自己,露出頭面惡狠狠緊盯著那錦衣公子,右手就按在鞍後刀柄上。
高楞子在此地並無舊相識,又兼對方出手前毫無徵兆,直接就打也不報號,眼看事發蹊蹺,馬寶華從馬車上躍下,幾步趕到近前喝道:「住手!」。
騎馬公子的僕從似乎也並不想惹事,沒有出言阻攔,而是直接拉著馬慌忙閃避,要從官道上下去,直奔並沒有路的莊稼地而去。
那公子儼然對自己僕從的逃避表現極為不滿,勃然大怒,坐在馬上奮力拉扯著韁繩喝道:「你倆不用管我,去把他們的腦袋都給我摘下來!」
此言入耳,眾人都是大驚失色,眼下的世道不太平,遍地頗有些占山吃水的綠林客,富家子弟都流行雇傭些保鏢、護院隨身跟班,直隸更是習武之風盛行之地,好手諸多。這公子一開口就露了殺意,二來讓這兩個僕人要摘全隊十幾個青壯的腦袋,那此二人必定不會是庸手。
對方話音剛落,高楞子率先拉刀在手,丟開韁繩兩步躥到馬寶華的身邊,與他靠在一起,馬寶華也將從車上抻出來護身的花槍握在手裡。後面跟著車隊的夥計們紛紛下馬,拉刀拎棍地護在車邊。鄒掌櫃的則一個翻身爬在貨包後面,慌張地向四下瞭望,看是不是有賊人在旁邊埋伏接應。
變生突然,諸人都感覺這是中了埋伏,恐怕眼前這三人不是什麼富家公子,而是賊盜們放出來探路的「誘子」。車隊的眾人都懷了搏命拚殺的心思,就等著埋伏的賊盜一躍而出,兩方對陣真殺實砍,命大的全鬚全影,倒楣的命喪異鄉。可片刻之後,跟在這公子身邊的兩個僕人,不但沒有上前動手,反而面色慘白轉頭就跑,一頭扎進過人高的玉米地裡,只看得見玉米杆子如波浪般分合起伏,轉眼間就再也看不到蹤影。而路兩邊的田地裡也是靜悄悄一如往常,根本沒有什麼伏兵躍出。
眾人不由得一愣,再等了幾喘息,看四下的確無人,方才那兩個人也跑遠得蹤跡不見。
馬寶華一使眼色,高楞子上步伸手抓住那公子的腰帶,就要揪他下來。那公子慌忙道:「別拉我!我是好人!恩公救命啊!」
還有賊喊救命的?通常賊盜要是失手被擒了,骨頭軟的傢伙看落在誰手裡會有不同的告饒喊法。落在江湖同道手中要喊「好漢饒命」;落在巡防兵勇手中要喊「官爺開恩」;落在本家或事主手裡要喊「小人知錯」,卻沒人會喊「恩公救命」的。
馬寶華心中起疑也跟著上前,卻發現這公子的兩腳被綁在馬鐙上,左手被綁在馬鞍上,只空著右手捏著根馬鞭子。馬寶華忙指揮人把他解下來細問究竟。
原來這位錦衣公子是位旗人,姓哈,排行第七,家住天津老城裡的鈴鐺閣後身,也算是名門大戶。前幾天老父親外派他去廊坊那邊收帳,可哈家是大宅門,嫡庶子弟之間的明爭暗鬥他早有心悸,仔細計較一番後,他先派了夥計帶了帳本走大路出城,自己另帶著夥計走小路。果不其然,走大路的夥計半路被人蒙面攔住,不搶金銀不傷人,單把帳本給撕爛了,這意在攪黃他的差事,要他回家在老阿瑪面前難堪。可這也難不住七少爺,他就這樣空著兩手走到了地方登門,當著對方掌櫃的面提筆蘸墨,憑著記憶硬把帳本又默寫了一份出來,兩相對照分毫不差,對方心服口服,無奈只得按帳結款。
可躲過了自家人的暗算,卻沒躲過江湖上的壞人,走過樹林的時候七少爺被方才兩人躍出將夥計打倒,捆住了自己索要錢財。他推說銀錢藏在客棧的炕洞裡,要帶著兩人回程去取,這兩人怕他跑了因此把他綁在馬上,裝作陪同出門伺候起居的下人緊緊跟著。七少爺遠遠看見鄒商戶的車隊迎面而來,心想這是個逃生的機會,這才演出了場借虎驅狼的好計。方才被他故意找茬鬧起來,這兩個賊人見這邊勢大,害怕所做壞事敗露落荒而逃,這位七少爺才僥倖逃出生天。
說到這裡高楞子忍不住怒然問道:「前面也有過去的客商,你咋就偏找上我們呢?你咋還抽我一鞭子呢?」
馬寶華拍拍他肩膀道:「算了,這位少爺也是心智過人,他是一來見咱們人多,求生的把握大些,二來他老遠見你腳上穿著兵勇穿的靴子,知道你必然不是個慫包,所以才找上你的。要是換了旁人,還真未必敢跟他們動手呢。」
這話說得正是七少爺心中所想,還真是他方才危急中靈機一動的心思,吃驚之餘,七少爺不由多看了馬寶華幾眼,向高楞子賠禮,並許諾到天津後必有報答,便走過來客氣相問。
馬寶華也抱拳答禮:「在下馬寶華,一介草民,之前在淮軍給營官做過幾年親兵隊正,從甘肅退了軍籍回天津老家。」七少爺聞言眼光一亮,在馬寶華身上上下打量幾眼,重又規規矩矩地見了一禮。
眾人規整車輛重新上路,與七少爺結伴同行。
高楞子走了會兒,夾了夾馬肚走到身邊低聲問七少爺道:「那兩強盜沒搜到你的錢啊?你把它藏哪了?」
七少爺看了他幾眼,見高楞子眼眸黝黑眼神真切,看得出他是個實心眼的孩子,所問也是無心,便嘿嘿一笑,舉起手裡這條精編烏杆的馬鞭,將鞭杆後面的堵頭拔下來,把塞在空心裡面的幾張銀票摸出來放進懷裡道:「藏這裡了。」
高楞子愣了會子嘆道:「你可真精明,不藏在身上啊,這就是在你身上搜上一天也搜不到呢。」
七少爺見他樣子憨實,又為之前抽他那一鞭子有些歉意,低聲道:「好兄弟,等回了天津我交了帳,自有好東西送你做酬謝,金的、銀的隨你選。」
誰知高楞子搖頭手指馬鞭道:「別的我不要,我就要你這個!」
七少爺雖有些不明所以,卻還是伸手將馬鞭遞到高楞子手裡,真就送給了他。
高楞子拿了馬鞭很是歡喜,轉過頭來走到貨車旁邊揚了手對馬寶華道:「哥啊!在甘肅你不是一直想尋個好馬鞭子麼?我朝人家要來了,給你用吧。」
馬寶華笑道:「楞子,咱都出了軍營多遠了,到了家哪還再有馬可騎啊。你自己留著吧!」
高楞子想了想,低頭嗯了聲,將馬鞭揣進自己懷裡。
車隊進了天津城,大家欣然散夥,鄒掌櫃帶著貨物去交割,七少爺回家交帳,臨走問清了馬寶華的住址,一再保證要上門感謝。
等眾人都走了,馬寶華低頭思量了片刻,拉過來高楞子將自家住址跟他說了一遍,然後指給他南市方向,說那裡好玩,可以聽書、看戲、吃小食,要他先去那裡玩上一圈,到晚飯後再按著地址找上門來。
高楞子聽話,轉身順著他手指的方向就去了。
馬寶華暗自出了口氣,這才邁步向家中疾走。馬寶華是個心思多的人,遇事習慣多想想,他這番安排並不是要捨棄高楞子,而是有他自己的道理。
畢竟自己四年未曾回家,心裡最怕的就是斗轉星移物是人非,萬一家中出些滿園春色躍出高牆的事情,被自己突然回來撞見,可不太好說,所以還是把外人支開穩妥些。再者是夫妻多年久別,必會有些親暱的事情要做,留著高楞子在身邊也不大方便。況且自己帶著這麼大一個生人回來,妻子什麼態度事先也未及商量,所以還是讓他再外面轉轉再回來,更方便些。
馬寶華走進胡同口,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古人說近鄉情怯,一路來離家越近,他這心越是發空,身在胡同外,心裡是滿腔抑制不住的欣喜,卻有種不敢向前的畏懼感油然而生。不知道這些年娘倆過的如何?女兒可曾長高?院子裡如何的擺設佈局,是不是跟自己當年走時一模一樣?
旁邊院門打開,走出來個乾瘦的老年男子,見馬寶華呆立在不遠處不由得一愣,待攏目細看清了面目,驚訝道:「寶華兄弟回來了?不是有消息說你死了麼?」馬寶華回頭看了看道:「孫大伯啊,我沒死啊,我好好活著呢!」孫大伯將辮子在脖頸間一繞,疾步走過來按住馬寶華的肩膀感慨道:「真的是你啊!你還活著啊?你快回去看看吧,這幾年你家女人帶著孩子過得可難啊!」他回頭又嚷道:「老婆子,寶華回來了!趕緊的,找找有沒有紅粉皮、木耳、麵筋啥的,給他找點,讓他們家今天吃喜麵!」
馬寶華按了按勒在胸前的包袱帶子,大步推開家門,高呼道:「媳婦,我回來啦!」幾個好熱鬧的鄰居們也跟在他身後往裡張望著喊道:「寶華回來啦,你們娘倆終於盼到享福的時候了!」
院子裡寂靜而蕭肅,拾來的柴禾在西邊牆下堆著,窗戶紙上被風捅破的窟窿黑洞洞瞪視著闖進來的陌生人,屋頂上瓦隙間鑽出來的茅草亂紛紛有巴掌高,並無人應答馬寶華的呼喊。
馬寶華的心便往下沉,他記得自己臨走的時候,院子裡有水缸、有石磨、種著小蔥和香菜,還有手腕粗細的葡萄藤,搭起來的架子能陰蓋住半個院子,這些都哪去了?一瞬間他恍惚有些懷疑自己是否走錯了地方。
他又喊了兩聲,屋門猛地打開,一個身穿件帶了補丁的土布衣裙的蓬頭女子站在門裡,怯生生地朝外看過來。
馬寶華心中一疼,幾步快走過去,托住那女子的小臂,喊道:「翠芹,我回來了!」
杜翠芹久盼丈夫回歸,驟見之下心頭悲喜交加,腹內情愫翻湧激盪,只覺一陣暈厥從腳下傳上來,身子晃晃幾乎摔倒。
馬寶華連忙伸臂將妻子攬進懷裡,一隻手抱住她的腰,另一隻手輕撫她的後背,盡在她耳畔安撫道:「不怕不怕,這次回來就再也不走了。咱們一家人好好過日子,就再也不分開了。」
周遭的街坊們都是看著杜翠芹這幾年如何艱難度日的,今遭見她夫妻二人終於團聚相擁,都很有些唏噓感慨。
正在這一刻,屋內傳來輕輕的腳步聲,一個七歲大的小女孩,懷抱著不足一歲的嬰兒怯生生自屋子裡走出來,小聲問道:「媽媽,他是誰啊?」
馬寶華聞言轉頭,先是驚愕、繼而憤恨、更兼惱怒,他猜得到這小女孩是自己當年離家時不滿三歲的女兒,如今也應長到這般高矮。可是自己四年未曾回家,這不滿一歲的嬰兒又是從哪裡來的?
他劈手揪住杜翠芹的衣領,用力拎到自己眼前喝問道:「這抱的是誰……這小的是誰的孩子?」方才還是夫妻團聚溫馨安撫,眨眼就橫眉立目翻臉變色,這瞬間翻天覆地的變化,令杜翠芹面色蒼白眼神散亂竟說不出話來。而這般表情看在馬寶華的眼中,更是堅實了他心中一路的猜疑與恐懼。
從甘肅回來他最怕的就是這個,怕妻子耐不得清苦做出些有損名節的事情,可沒想到真是怕什麼來什麼,這鳩占鵲巢的事情不但發生了,居然連孽種都有了!馬寶華此時牙關緊咬,卻壓不住漲滿全身的怨怒之氣,他左手狠狠一推,將杜翠芹按在門框上,右手握住了腰間護身小刀的刀柄:「妳這臭婊子快說!這野孩子是誰的?」
杜翠芹面色慘白如紙,背倚著門框全身顫抖,若是沒有馬寶華揪著她的衣領便要癱倒在地。她仰望著馬寶華近在咫尺卻因憤怒扭曲的面容,渾身上下只剩得輕輕搖頭的力氣,說不出話來,只淚水如泉,湧眶而出。
共1頁: 1